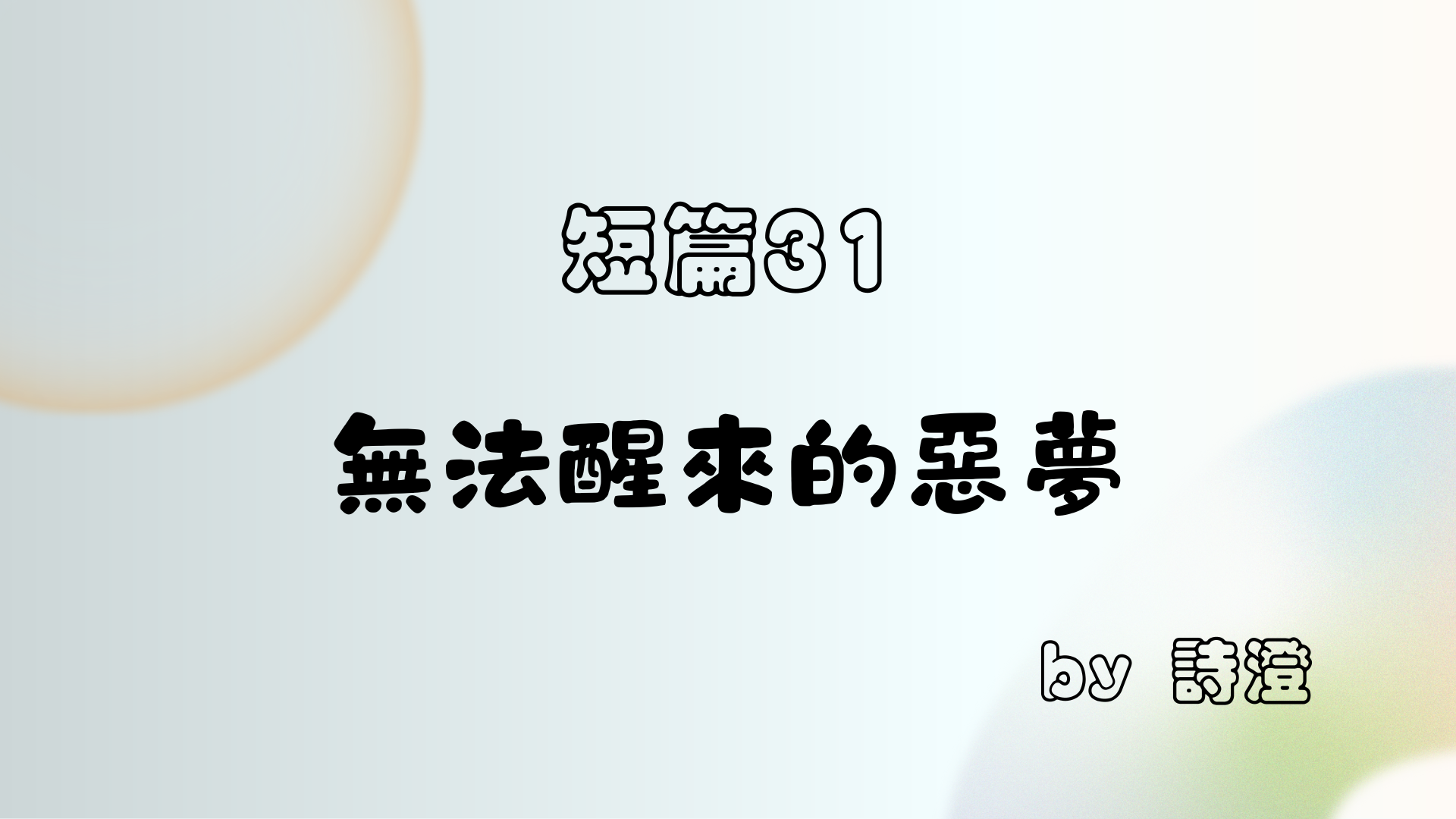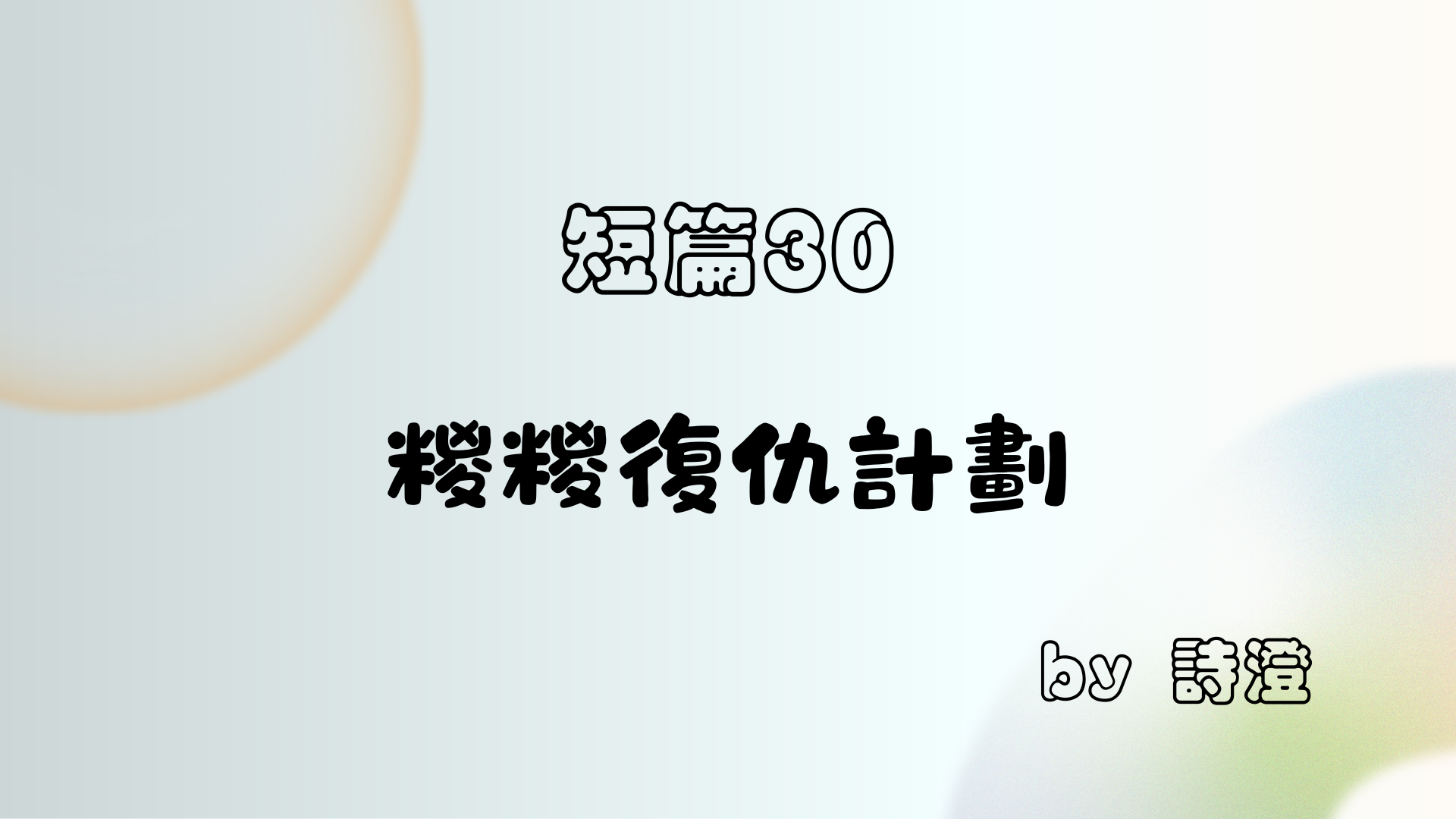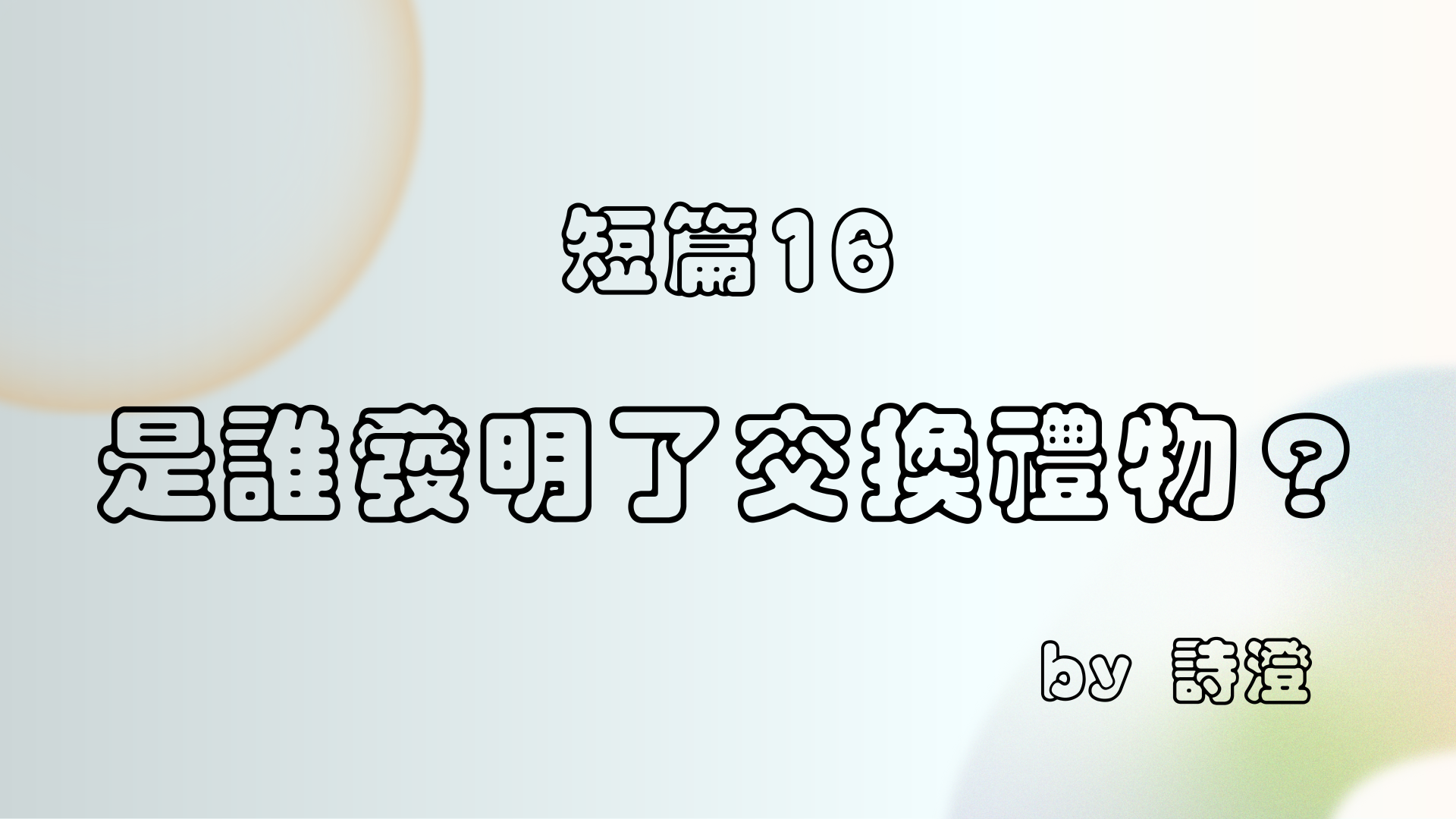在這個無月之夜,橡樹林中霧氣纏繞。沒有清風吹動草葉,只有遍野朦朧像幽靈般起伏飄移。連影子也是模糊的,沒有明確的界線。就如同樹下的一男一女,此刻沒有你與我之分。雙握的十指、交疊的身軀、融合的汗水……一切都合而為一,化為一陣又一陣令人銷魂的愉悅。喘息聲、呻吟聲,此起彼落,間中夾雜一聲壓抑的呼叫。接著聲音停止了,動作也停止了。男人站了起來,撿起了他的褲子並且穿上。而女的則仍軟癱在地上,輕抽著氣,餘韻未止。
男的又抓起那勾著橡子、沾滿碎葉的裙子,把它丟到女人身上,接著便說:「妮娜,換個地方是不是特別刺激?」
女人以裙子遮掩飽滿的胸部,坐起來媚笑道:「刺激到極了,連你的表現也威猛起來啊!」她套好無名指上鬆脫的指環,向男人打了個眼色:「明晚也帶我來,好嗎?」
男人的臉上現出一個猥褻的笑,然後來到女人身邊,用粗糙的手指抵起她的下巴:「你真不得了!不怕你丈夫發現嗎?」
女人甩開他的手,卻笑得更媚了:「怎麼會發現?他早就和我分房而睡了!」
男人粗魯地摸著、捏著女人的臉:「太浪費了!真的太浪費了!那傢伙真沒用!好,我明晚來接你……」
說到這裡,女人的忽然瞪大了眼睛。神情驚駭,連臉也僵住了。男人被這表情一嚇,連忙轉過身去。猛然見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正的站在他身後。然而熟不熟悉並不是重點,重點是——那人正雙手握著斧頭,並高高舉到頭上,好準備隨時劈下……
當聽見長長的牛叫聲時,森普斯理解到就近有地方可供落腳了。雖已經很累,但他還是收起了手杖,加快腳步向前走去。雖然知道這一帶沒有城市,也沒有鎮子。但即使只是鄉村的麥桿床,他已經覺得很好了。在今次的旅途中,大部份時間都身處荒野,連找個乾爽的地方也難。他下定決心,無論前面是個怎樣落後的村子,都要至少待上三日三夜。
走了約三十步,他便從橡樹幹間窺見了村子的形貌。這是個以種麥為主的的農村,在這時節麥子都收割完了。有些田地變成了放牧的地方,有些則種了豆子和苜蓿。有些房子零散地建在田地間,也有些集中在一起,成了村子的主體。道路貫穿其間,通向一道長長的斷崖。而崖間水霧在飄,下面原來暗藏著一條洶湧的河流,而水霧後則是一排近乎黑的深綠。
森普斯繼續前行,轉了個彎,便見到村口。路邊的木牌上刻了幾個字——橡林村,用來形容這個地方也滿貼切的。由這裡起,道路便由泥土變成了沙石地。村民在上面走過,推著單輪斗車又或是趕著豬,臉上的是對旅人的懷疑和好奇。森普斯微低著頭靜靜向前走,以免惹來村人的不快。
可是這時,村中出現了爭執吵的聲音。是一名老者在大聲說:「絕對不可以!我們不可以到對面去!」
本以為是兩個人在爭執,但森普斯一抬頭,便發現那原來是兩幫人。一幫是中老年人,而另一幫則是青年人。前一幫無容置異要比後一幫要衰老、虛弱得多,但他們的神態又那麼強頑,不見得是處於劣勢。
剛才那名老者似乎是同幫人的領袖,他站在最前方繼續代表眾人說:「若到對面去,我們就會受到上帝的懲罰!你這樣是想拖垮村子嗎?」他眉頭緊皺,似乎很是生氣。
在年輕人當中有一個約二十歲出頭的金髮男子,他用手指點著自己的腦袋說:「老頭子!我拜託你用用腦子才說話吧!拖垮這條村對我有甚麼好處?」
老者氣結極了,指著對方大聲道:「你……你叫我老頭子?」
金髮男子用同樣大的聲音說:「是呀!我叫你老頭子!因為你的確是老嘛!」
老人衝上前去要揮拳打那年輕人,卻被同伴拉著。
而年輕人則囂張地向老人聳了聳肩,還攤開雙手說:「儘管來打我啊!我接受你的挑戰!」
沒有人阻止他,其他年青人在一旁竊笑。原本看來充滿自信的長者,現在都紛紛表現得畏縮了。形勢被扭轉過來,被抓著的老人大罵對方是「不知輕重的死小孩」、「口出狂言的臭流氓」,看起來就像是頭被戲弄的狗。
森普斯實在看不過眼,那年輕人實在過份。然而他只是一個路過的旅人,又可以幹些甚麼?就算走上前維護那老人,對方也不見得會接受他的好意。這就是小農村的習俗——排外,經常四處遊歷的森普斯對此很是清楚。
這時,一名中年婦人自田地那邊跑來了。她來到兩幫人中間說:「好了,你們別吵了!」她面向著金髮年輕人:「安貝羅,就當是看在我的面上吧!諒我是你亡母的朋友,你就聽我一句,別再惹村長了,好不好?」
森普斯感到很驚訝,原來那老人竟是村長!但堂堂村長,為何卻沒得到後輩的敬重呢?這似乎不太正常。
那叫安貝羅的年輕人把雙臂疊放在胸前:「好!我就少罵他幾句!但我的計劃還是依然會繼續的!」他說完,便和其他年輕人一起轉身離開了。
村長等人瞪著他們的背影,接著在原地低聲相討著甚麼。森普斯不好意思上前去聽,於是只好放棄。他往另一邊走去,進了村子裡唯一的旅店。店子一樓是小餐廳,有兩條長方木桌。沒有靠背椅,用的都是長木凳。同一層還有廚房,而二樓應該就是宿房吧。森普斯沒有馬上要房間,而是先坐下來,叫掌櫃的中年人給他吃和喝的東西。掌櫃的拿來了雜糧麵包,還有蔬菜稀湯,不等客人開始吃就先收了錢。森普斯只給了他一丁點小費,但他似乎就已經很高興了,森普斯於是便順口問起了剛才外面的事。
掌櫃的說:「都是為了一道橋啊!安貝羅——就是那個金髮的小子,堅持要建一座橋通到對河那邊。但這怎可以呢?不可以的,絕對——」他加重了語氣,一字一字的說:「不.可.以。」
森普斯一面嚼著發硬的麵包一面道:「他為甚麼要建橋?一個小伙子,怎會沒事沒幹生起這種念頭?」
掌櫃不屑的說:「他有錢嘛!有錢人就是愛耍這種任性,以為只要他喜歡,沒甚麼是不可以做的。依我說呀……他根本是個外人。你看見嗎?他那把頭髮,那種衣裝,那種態度,有哪裡像是本村的人?」
森普斯往外望去,遠遠的見到安貝羅站了在街角。的確,他的外表顯得比任何人都要時髦。頭髮很整齊地梳向同一邊,穿著一件沒甚麼實際用途的短背心,腳蹬一雙新淨的皮靴子。怎麼看都是一個城市人,而非在農村土生土長的青年。他說起話也滿刻薄的——城市人式的刻薄,而不是鄉下人的那種粗俚。
森普斯用湯來把麵包泡軟,接著便見到安貝羅向這邊慢慢走來。森普斯望著他,繼續問掌櫃:「那麼村長呢?他剛才好像說到甚麼上帝的懲罰。」
掌櫃怪叫一聲:「不是『甚麼』上帝!上帝就是上帝!」
森普斯趕忙修正:「啊!對,對,是上帝的懲罰。」
掌櫃雙手按著桌子,俯低身子面對著森普斯:「這絕對是真的,我可以向你保證。從來沒有人能夠去到河對面,妄想要過去的人,都會受到懲罰。」他壓低聲音,故作神秘的說:「就在十年前,村長也想過要築橋的。只是後來……」
這時,旅店的門被大力拍響了。是安貝羅,他正側身靠在門邊,板起臉孔瞪著掌櫃。
掌櫃見到他,就慌忙站直了身子。接著又哈著腰,連連向安貝羅點頭道:「老闆!有甚麼吩咐?」
森普斯聽了,差點被湯噎到。掌櫃剛才還在說安貝羅的壞話,森普斯實在沒想到他原來是旅店的主人!但這也證明了他的富有,可以擁有一間旅店,而且還能令一個看不起他的人,委委屈屈地為他工作。這就是錢的魔力,是窮人所渴望而又做不到的。
安貝羅沒瞧森普斯一眼,冷冷的向掌櫃說:「我的房間沒租了出去吧?」
掌櫃的連忙道:「沒沒沒!而且已經打掃得很乾淨了。」
安貝羅沒作回應,邁步在森普斯身後經過,接著踏上了樓梯。走到一半時,他停下了腳步,從腰間的錢袋裡掏出一個銀幣。掌櫃頓時眼都亮了,仿佛是頭在餐桌邊等候骨頭的狗。安貝羅把銀幣拋過來,正正落在掌櫃的手心中,接著道:「工作辛苦,拿去吃些好的吧!人不說話是不會死的,但不吃東西就會死了。」
掌櫃的連連鞠躬道謝,安貝羅接著便繼續上樓梯,在二人的視線中消失。等腳步聲、開門聲、關門聲都消散了後,掌櫃才轉過身來,聳聳肩向森普斯說:「你也聽見了吧?我不能告訴你更多了。」
森普斯也不想勉強,於是便靜靜的喝完他的湯。然後,掌櫃給他安排了房間。安貝羅的房間在最左方,窗子面對著村門外。而森普斯的的則在最右方,窗子向著村子中心。掌櫃似乎是怕老闆不滿,所以才這樣安排。
之後的時間,森普斯都在忙自己的事——到村外尋找藥草,好將訊息賣給行醫的友人。從行囊中拿出筆記本,檢視今次的行程。還有檢查食水、乾糧的數量等等。打後吃過晚飯,然後便腄覺去。
第二天早上,一陣嘈吵的聲音自窗外傳來。又是爭執的聲音,而且非常激烈。森普斯把頭伸出窗外,見到以安貝羅為首的一群年輕人,將村長的家團團圍住了。村長人在大門前,正被安貝羅揪著衣領脫不了身。其他老年人在一旁焦急地看著,想救人卻又無計可施。
安貝羅揮了一下手,大聲道:「這混蛋不配做村長!來,給我把牌子拆掉!」
幾個年輕人一湧而上,把村長家門前那寫著「村長的家」的老舊木牌給硬扯下來。牌子被重重的丟到地上,被人們當成洩憤對象狠狠地踐踏。
村長一面掙扎一面大吼:「你們幹甚麼?我是村長!你們怎可以對村長動手的?」
四周的老年人終於也粗著膽子鼓譟起來:「對啊!怎可以對村長不敬的?他是大家選出來的領袖啊!」
安貝羅冷笑了一下,接著用極為不屑的語調說:「大家?哪個大家啊?上次選村長已經是十五年前的事,所謂的『大家』就只是指你們這些老頭嗎?而我們這些年輕人,就不算是橡林村的一份子嗎?」
支持他的年輕人都連連稱是,還有人說:「上次教堂在火災中被燒毀,都是因安貝羅出錢資助才能夠重建的!」
另一人亦道:「還有啊!前年小麥歉收,都是因為安貝羅仗義相助,我們才捱得過來!而我們這個村長,卻甚麼都沒做到!大家說,誰才有資格做村長?」
年輕人都舉起手臀,大呼著:「安貝羅!安貝羅!安貝羅!」
這時,村長忽地一拳打到安貝羅的臉上!安貝羅慘叫一聲,鬆開手跌了開去。村長趁此時機,馬上飛奔離去。安貝羅一面詛咒著,一面按著流血的鼻子。搖搖晃晃的站起來,指著村長的背影大吼道:「死老頭!別跑!我不會放過你的!」說完,便追在村長後面。
其他人——不分老幼,亦都追上去了。森普斯匆匆離開宿房,跑下了樓梯。見到掌櫃的一副氣定神閒的樣子,在櫃台後打著呵欠。他雖亦看到外面的鬧劇,但似乎已下定決心置身事外。
森普斯衝出門口,剛好見到村長和眾人跑進了樓房間的小巷中。森普斯沒跟在他們尾後,而是預測他們的路線,然後調頭往另一邊跑。當眾人由另一條巷跑出來時,森普斯剛好擋了在村長和安貝羅中間。他把後者撲倒,二人滾到一邊去。眾人大吃一驚,都站住不再追了。村長也停下了腳步,轉頭看到底發生了甚麼事。
森普斯坐了在地上,從後抓住了安貝羅。一手環抱著他的頭頸,一手攬著他的雙手和腰腹。安貝羅動彈不得,只得胡亂踢著腿,大嚷道:「放開我!你這個多管閒事的遊民!我要好好教訓那死老頭!」
森普斯回應道:「就是這樣我才不可以放手啊!我怎可以眼睜睜看一個老人被打?」
安貝羅大叫道:「那看著我被打就可以啊?」
森普斯說:「是你帶頭包圍村長的家吧?你先犯人,人家自然也會犯你!」
安貝羅掙扎著:「但我的橋怎樣?我的橋就不用管了嗎?那死頭,竟敢動手破壞我的橋,想逼我放棄!幸好我發現得早,要不是就前功盡廢了!」
森普斯聽到村長破壞橋樑,頓時呆了一呆。在一般的觀念中,村長應是建設村子的人,為甚麼這個村長卻要反過來破壞?他想起了昨天聽到的話——若果到對面去,我們就會受到上帝的懲罰。
森普斯的手稍稍鬆開,安貝羅便馬上掙脫掉了。但他沒衝上前打村長,只是站起來抹掉鼻血,把身上的沙塵拍去。接著指著仍坐在地上的森普斯說:「我警告你!別再插手這件事了!你只不過是個外人罷了,這兒的事不到你管!」
森普斯被他的態度惹毛,站起來拍掉臀部的沙,然後冷笑道:「你有比我好很多嗎?城市人!」
安貝羅的臉頓時白了,想反駁卻說不出話來。經過一輪沉默,他便猛的轉身,踏著重重的步伐離去。
上次那名當和事佬的婦人,跟在他們後面:「安貝羅,你聽我說……」但安貝羅對她不瞅不睬。
其他年輕人也跟上去了,當中有些人回過頭來,向村長、森普斯等人報以鄙視的表情。森普斯懷疑是否應該再在此地逗留,因為在這種偏僻的地方大多沒有王法。觸怒了本地人的結果會是甚麼?輕則被打一頓,重則……
正當他在思索時,村長來到他的身邊:「這位小兄弟,你是……」
森普斯回過神來,回應道:「我叫森普斯,在旅途中剛巧路過此地。」
村長拍了拍森著斯的手臂:「真的很感謝你。」接著又望向貝安羅離開的方向,悶哼一聲道:「這班小伙子簡直目無尊長!」
森普斯問:「你有沒受傷?我剛才見到……」
村長揮揮手道:「不,沒事,那群小子太小看我了!對了,為了答謝你,不如來我家吃頓飯吧!不用給我客氣的!」
森普斯這才發現自己的肚子扁扁的:「好吧!說起來我還未吃早飯呢!」
其他人都逐漸散去,而森普斯則跟著村長,來到先前事故的發生地點。寫著「村長的家」的木牌子,依然趟在地上。村長把它拾起來,拍掉了灰塵,再豎著擱在門邊。臉上的灰鬍底下木無表情,但他的話語表現出他的唏噓——他凝視著牌子說:「十五年來,我都沒受過這種侮辱。」
森普斯沒有甚麼想說的,因此只是保持沉默,接著村長便領森普斯進屋子裡去。那是一間很普通的房子,以木框搭成主結構,其餘的地方用磚、泥建成牆壁。屋頂是幾條橫樑,上面舖著樹枝和乾草。傢俱也非常簡陋,只有一張桌子、兩條枝凳、一個大木箱子。另外還有左右兩個房間,裡面都放了床。但其中一間顯然沒人住,床上沒有乾草更沒有床單,上面更堆滿了柴枝、斧頭等雜物。另外還有一道門通到屋後,爐灶等東西就在那兒。房子雖有窗,但都很細小而且向西。因此即使是在大白天,還是昏昏暗暗的一片。
森普斯坐到板凳上,而村長則去到屋後準備煮食。森普斯聽到他在切菜,還有水倒進鍋子裡的聲音。過了一會,村長便用布著擦手,來到森普斯對面坐下來道:「正在煮湯,另外還有麵包。」
森普斯點了點頭,預計得到這一餐和旅店的大概沒有兩樣。農村就是這樣子,他也不妄望會有更好的。
村長把布掛在桌角,接著主動提起了村裡的事:「這種日子真不知何時才會過去……沒有一天是安寧的,我看我就算死也不會眼閉。但我若現在就退下來,不再當村長了,結果會怎樣?安貝羅那傢伙一直在盯著這個位,他相信只要當了村長就可以任意妄為。」他搖了搖頭,長長的嘆了口氣。
森普斯乘勢問下去:「我聽人說過他想建橋!這對村民來說應該是件好事。但我實在看不過眼他的態度,若果他肯改善一下……」
村長重重的揮了一下手:「改也沒用!不管他是甚麼態度,橋都是不可以建的!你是外人,所以你才不知道。但村裡老一輩的,都知道對岸是甚麼一回事。那是被詛咒的土地,是人不應該去的另一個世界!去過那邊的、或是想去那邊的人,都不會有好下場!」
森普斯看著對方那陰沉的臉,問道:「你這麼肯定?」
「當然!」村長頓了一頓才道:「我就親眼見過……不,我本身就是受害者。其實在十年前,我也決定了要建一條到對岸去。然而工程開始了不久,就發生事故了……」他用手揉著雙眼,揉得眼睛都紅了:「讓我告訴你,我原本有兩個兒子。」
森普斯的目光在村長的臉旁掃過,投到那張放了柴枝的床上。
村長直盯著森普斯的臉:「當時一個十八歲,一個十六歲,都參加了建橋的工程。然而有一晚,我的長子在獨自巡察工地時掉了下去,被尖木刺死,到天亮時才被村民發現。」他連連搖著頭:「我是很傷心,但認為這只是一次意外。工程為此而停了一段日子,然而工作再次展開時,更嚴重的事故發生了。」
森普斯俯前身子問:「你的次子也出事了?」
村長點點頭:「不止他,其他人也出事了。當大家正要舖設橋面時,支架突然鬆開、倒塌。我永遠也忘不那個景象……隆隆的聲音、往下直墜的木材、還有年輕人們的驚叫。」他遞起食指往前一指:「這一切就在我面前發生,十個年輕人——包括我的兒子,都掉到崖下。崖雖然並不很深,但石頭很多,水也急。加上塌下的木材……你可以想像得到那個情景,要有多恐怖,有多慘烈。」
森普斯微微垂下頭:「我感到非常遺憾。」
村長豎起兩隻手指:「兩次事故,十一條人命,就只是為了一條建不成的橋。所以我破壞安貝羅的工程也是逼不得已,我不想再有人犧牲。」
森普斯問:「但你肯定那不是純粹的意外?」
村長的神情變得更陰沉了,看起來就像個含冤而死的亡魂:「你不相信我?」
森普斯微微遞起雙手,搖搖頭道:「不,我不是這個意思。只是太過好奇,想問得更清楚罷了。」
村長的臉色緩和了一點:「目擊事件的人都相信,這是上帝的意旨。上帝不准我們過去,因此給予我們懲罰。」
森普斯點著頭和應著:「上帝的意思是不可違抗的。」
村長聽了之後,就變得和顏悅色了:「因此,我不惜一切都要阻止安貝羅建橋。這是為了村民,為了村子。我見過那場悲劇,一次已經太多了,我不想見到第二次。」他抬頭,表情又變得無奈起來:「但是那群小子已不放我在眼內了,反正就是看不起我窮,見到有錢的人便靠過去。在這時代,人心已經可以用錢來買了。」
森普斯用手支著下巴:「一連失去了兩個兒子,你一定很痛苦。」
村長垂下眼皮:「是啊,自此這個家就只剩我一人了。因為我的妻子也因過度傷心而病故……你可以想像,這些年我活得有多苦。支撐著我的生命的,就只是一顆想要維護村子的心。」
接著,他們便用了餐。分別之後,森普斯便回到了旅店。本以為安貝羅會把他這個多管閒事的人轟出去,然而森普斯並沒有遇見他。掌櫃也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仿佛時間根本沒流動過。森普斯回到房間,在筆記上描繪他的藥草地圖。
然後黃昏漸逝,夜就像一塊黑布般蓋過大地。然而一彎新月升到天空中,以溫柔的光照耀凡世。在底下,人們吹熄油燈,鑽進被窩安然入睡。整條村都變得非常寂靜,然而旅店中卻響起老舊地板的嘰嘰聲。
是森普斯,他雖盡量放輕腳步,但還是免不了會發出聲響。一步一步的踏下樓梯,就像是在懸崖邊走路一樣小心。他經過長餐桌,再經過櫃檯。輕輕的推開半道門,便著便溜了出去。他四周打量了一下,確定沒有弄錯方向,便朝河的方向走去。關於橋的事他已聽過了,但卻沒親眼看過那個地方。然而在白天去看,可能會被安貝羅找麻煩,因此他決定在晚上行動。
村子並不大,因此他很快就到達了。橋的支架就屹立在面前,由此岸連到彼岸。對於鄉村而言,這已經是一個很大的工程了。從支架之間望下去,只見到底下一片漆黑。隱約見到幾塊大石,流水在衝擊著它。發出湍急的水聲,以及陣陣令人身心俱寒的涼氣。就是這裡,曾經枉死了十一個年青人。
森著斯閉上眼睛,想聽聽亡者的呻吟。然而他並沒聽到想聽的,只聞背後傳來輕輕的腳步聲。他回過頭來,見到的是安貝羅。他就像白天時那樣衣履整齊,而雙手則交叉放在胸前。他見到森普斯,但沒有發怒,只是用平靜的語調說:「我無論如何都會建好它。」
森普斯但頭凝視著深淵似的河谷:「不怕犧牲?」
安貝羅抬頭望著興建中的橋樑:「我根本不相信。」他頓了一頓,繼續道:「別以為我只是個不信神的傢伙,其實十年前那場意外發生時我也在場。」
森普斯感到滿驚訝的,望著安貝羅那年輕的臉:「十年前?那時你幾歲?」
「十二,我是在這條村出生並長大的。」安貝羅望向森普斯,臉上是無奈的表情:「村民向你說我是城市人,對吧?」
森普斯點了點頭。
安貝羅再次望向橋樑:「是地道城市人的其實是我父親,有一次他路過此地,結識了我的母親。他們相戀了,但他不得不回去,而母親卻捨不得這地方不肯跟他走。於是他們在此結婚了,他回到城裡,而母親則留在此地。」他的臉上泛起一點笑意:「但他是個負責任的人,他每年都回來這裡探望我的母親,後來還生下了我。到我十三歲時,我母親病死了,他於是就接我到城裡去住。就是這樣,我離開了村子。」
森普斯問:「那現在呢?你搬回來住了?」
安貝羅說:「不,我長住在城市,只是偶爾會回來。但老村民都不當我是村裡人了。因為我父親是城市人,而我又離開過……村民的排外心都很強。」
森普斯感到黯然:「上次說你是城市人,真是抱歉。」
安貝羅微微遞起手表示不用介意:「但我希望重新融入村子,為此我又付出了多少?修教堂、建旅店、於荒年送贈糧食……我甚麼都做了。我的好意得到了同齡人的接納,但是老一輩的只認為我是用錢收買人心。難道和人分享也有罪嗎?不,我不覺得。」
森普斯的思緒和心情都複雜起來。
安貝羅吐了口氣,但站姿依舊挺立:「他們把自己封閉起來,排斥一切自己看不慣的東西。我對他們好過的,真的……事情發展成這樣不是我所願的。只是他們的態度,真的觸怒我了。」
森普斯說:「但萬一上帝的懲罰是真的?又或許不是上帝,而是陰靈作怪。」
安貝羅不屑的說:「只不過是迷信罷了!十年前的事,也許只是因為橋的結構有問題,因此會才會塌。但今次不同了,我請了這方面的專家來。」他踏前幾步來到橋邊,遞起手指向對面的黑暗:「你知道那邊是甚麼地方嗎?」
森普斯瞄著眼望向對面,使勁辨別黑暗中的景物:「是橡樹林?」
安貝羅搖搖頭:「不,是城市。只要過河,穿過橡樹林,踏上那邊的道路,我們就可以去到大城市。只要建成這條橋,商隊就會經過這裡,帶來繁榮和商機。到時村民不用再被天氣掌控一切,每天都光在祈求下雨或天晴。」
森普斯凝視著他,沒有說話。這時,那個充當和事佬的婦由村那邊慢慢走過來了。她站到安貝羅身邊,問道:「你怎這麼晚還出來啊?很危險的,萬一掉下去怎麼辦?」
安貝羅聳了聳肩:「沒事的,我很熟路。」
婦人說:「還是小心點好,村長的長子也許就是這樣掉下去的。」
安貝羅別過臉去,顯得不耐煩了:「又是說到他!」
婦人緩步走上前,輕拍著安貝羅的背:「你也體諒一下村長吧……他真的很可憐。先是妻子失蹤,接著兩個兒子又……」
森普斯頓感驚訝:「失蹤?村長的妻子是失蹤的?」
婦人望向森普斯,點點頭道:「對呀!這件事人人都知的。在十年前……也就是上次建橋的時候。沒有任何預兆,她卻從此沒再出現了。大家都有四處找她,但沒找到。」
森普斯喃喃道:「這就奇怪了……他向我說的是另一套。」
安貝羅和婦人面面相觀,一副莫名其妙的表情。
森普斯望向眼前這興建中的橋,似乎得到了甚麼啟示。他問安貝羅:「我可不可以到對面看看?」
安貝羅驚訝得瞪大了眼睛:「你敢過去?我還以為你信村長那一套。」
森普斯笑道:「我就是想證明一下。」
安貝羅考慮了一會,便道:「好吧!雖然橋現在只有一個主框架,還被村長用斧頭劈了幾下,但結構還是很穩固的,你可以放心踩上去。」他右手握拳,捶了一下自己的左掌:「但別想動手腳,我會在這兒看著直到你回來。」
森普斯微笑著向他點了點頭,接著便踏上了橋面。當他向前走時,木架不像旅店的地板那樣會發出怪聲,看起來真的很堅固。他回過頭去,向安貝羅豎起了大姆指。安貝羅掛起沾沾自喜的表情,為這條半完成的橋而感到自豪。這時,森普斯看到某幢樓房後,有人在向這邊窺視。然而天色太暗,沒辦法看到這是誰。但森普斯卻心中有數,他假裝甚麼也沒發覺到,繼續向對岸走去……
在這個晴朗的清晨,村長在自己的家裡拍桌而起:「甚麼?你今晚要到對岸去?」
坐在村長對面的森普斯說:「是的,因為我覺得未必是上帝的懲罰,冤魂也一樣可以令不幸的事件發生。假若真的是後者,我的朋友也許可以來處理一下。」
村長的胸膛起伏著,但他還是強逼自己冷靜下來。他再次坐到凳子上道:「你朋友是神父?」
森普斯微笑著說:「都差不多。但我想先親自到岸看一看,若果不是冤魂作怪,那就不必請他來了。」
村長的額上冒著汗:「但……那太危險了,萬一有事發生……」
森普斯拍著村長的肩:「放心,我是個四海為家的旅人,冒個險對我來說算得甚麼?但是有件事我要拜託你。」
村長問:「啊……是甚麼事?」
森普斯望了望門口,又望了望窗外,才壓低聲音道:「記緊,別把我的計劃說出去。我怕人們若來圍觀,萬一真的塌了橋甚麼的話,大家就會被波及了。我對自己應付危險的能力很有信心,但保護別人我可不怎在行。」
村長連連點頭,好像求之不得的樣子。然而他卻說:「但讓我和你一起去吧!我既是村長,又怎可以袖手旁觀呢?」
森著斯搖了搖頭:「不!正因為你是村長,所以才不可以去!萬一你出了事,就再沒有人可以壓制安貝羅這小子了!」
村長沉默了,過了一會兒才道:「那好吧……你自己小心。」
森普斯站起來:「我今晚出發,那時你就留在這裡為我祈禱吧!」他就完就離開了。
村長看著森普斯的背影逐漸遠去,接著亦站了起來。他進了沒人住的那個睡房,把斧頭自床上拿了起來,喃喃道:「上帝會保佑我的……一定會。」
夜又再一次到來了,月亮依舊掛在半空。在它的光芒之下,一個影子出現在村子的路上。是村長,他拖著沉重的腳步來了。手上是一柄斧頭,眼裡則是野獸獵食時的堅定目光。他聽到自己的心跳聲、呼吸聲是多麼的急促,但他的心依然保持著冷靜。就是這種久違的感覺,相隔足足有十年,然而他現在再次記起它了。
他沿著碎石路走去,在樓房之間通過。接著他見到了,那像墓碑般聳立的橋樑支架。四周一個人也沒有,但他知道那人就在對岸。他踏上了半完成的橋樑,慢慢向前移動。非常小心,生怕會被無形的手扯下去似地。瞄向下方,穩約還可以見到插在河心的腐木。那是上次意外時落下去的,事發之後也沒辦法撈上來。就那樣一直留著,記載著血染的歷史。
「上帝會保佑我的……一定會。」他喃喃唸著:「我只不過是懲罰有罪的人罷了。」
他一步一步的前進,終於來到對岸。這兒仿佛是另一個世界,沒有人煙,沒有農田,沒有牲畜。只有一片無盡似的橡樹林,水霧在四處徘徊。橡子被他踢到,在地上滾動。但他沒理會,繼續小心地前行。眼前就是繁盛的橡樹林,亂走的話可能會迷路,但現在不是想這個的時候。
他在找一個人,在天亮之前一定要找到。這時,他的右邊傳來了聲音。他連忙轉過身去,見到的是拿著油燈的森普斯。森普斯神情冰冷,和今早的親切溫和截然不同。雖有著同一雙淡棕色的眼睛,但看起來就像是另一個人——又或是一個鬼魂。
村長心中感到一寒,但還是擠出笑容:「我很擔心你,所以還是跟來了。」
森普斯的表情一點變化也沒有,只有雙唇開合著:「別再做戲了,馬尤.巴達先生。」
聽到這句說話,村長頓時驚愕得呆了。多少年來人人都叫他村長,但現在一個陌生的旅人卻叫出了他的姓名。
森普斯用平穩的聲調說:「你是在找我,還是在找這些東西?」他把油燈遞到左邊,自己沒進了黑暗中,卻照亮了地上一堆黃黃白白的東西。那是骸骨,人類的骸骨,和一堆殘舊腐爛的破布糾纏在一起。旁邊的地上還有一個洞穴,洞穴四周是被掘起來的泥和一把鏟。
村長的雙眼瞪大了,大得非常可怕:「你……你是何時……」
「昨晚就發現了。話說回來,昨晚在房子後偷看我們的就是你吧?」森普斯沒有等對方回答便道:「今早還假裝不知我已經來過對岸,你真的很會做戲。還有甚麼上帝的懲罰,都只是你瞎編出來的,對不?」
村長沒有說話,只是僵立在原地。額頭冒汗,眼瞪著森普斯。
森普斯的目光移到骸骨上:「一男一女……看起來已被埋了很久,骨頭上有被斬過的痕跡,很明顯是被殺的。女的還裸著身子,衣裙像裹屍布般包在外面,而男的則只穿著褲子。這代表著甚麼?他們在生時到底在幹甚麼?」森普斯的臉上浮現出冷酷的微笑:「當時的情形,一定令你怒火中燒吧?」
村長握著斧頭的手顫抖了:「不可能的……你……我……」
森普斯遞起加手阻止對方:「你可以甚麼都不說,反正我心裡已有定案。」他把加手伸進衣袋中,掏出一隻已鏽蝕變色的指環:「這是我在女死者指上發現的,裡邊刻著兩個名字——馬尤.巴達和妮娜.巴達。這個叫妮娜的,就是你那失蹤了的妻子吧?」
村長說:「你知道了她是失蹤的?」
森普斯聳了聳肩:「我並不聰明,只怪你自己說得太多。你謊稱妻子因痛失二子而死,是因為想取得我的同情吧?希望我這個這個多管閒事的旅人,相信你的說法,搞垮安貝羅的計劃。」他頓了一頓:「若果我沒揭發這個謊言,你會打算怎樣?利用我的同情心,借用我的手來拆了這條橋,然後自己又再裝無辜?」
村長的臉色沉下來了,眼睛也瞇了起來:「是誰告訴你的?她的事。」
「這沒關係。」森普斯踏前了一步:「是你殺死他倆的吧,馬尤.巴達。當年橋樑工程在進行中,他倆選中此地在此偷情。你發現了,於是用斧頭把他們斬死,然後就地埋葬。完事後你便回到村子中,向大家哭訴妻子失蹤了。」他晃了晃左手的油燈,光芒照耀在骷髏上:「而為怕埋在此地的屍體被發現,你於是極力阻止別人到這兒來。因此,橋也是絕對不可以建的。你於是製造事故,令人們相信只要築橋到這邊來,便會受到上帝的懲罰。但為甚麼要這麼狠心,連自己的兒子也要殺呢?難道……」
「沒錯!」村長打斷了森普斯的話,怒吼道:「他們根本不是我的兒子!一直以來我都感到很奇怪,為甚麼兩個兒子由小到大,既不像我也不像她!終於在那天半夜,我見到她悄悄偷走出去……她該死!他更該死!兩個孩子更應該死!」他眼裡充滿了怒火,嘴裡則喃喃道:「我只不過是懲罰有罪的人罷了!」
森普斯只是微笑,沒有說話。
村長用雙手握緊了斧頭:「你到底想怎樣?敲詐一個窮村長並不會得到甚麼。」
森普斯把指環握在手心:「只想給大家一個真相。」
村長舉起斧頭:「我不會給你這個機會的。」說完,就怒吼著向森普斯衝過去。
忽然,安貝羅從某株橡樹後跑出來。村長沒來得及做反應,就被重重的撞開。人摔到地上,而斧頭則飛了開去,深深的插到樹幹之上。接著,其他人也出來了。主要是支持安貝羅的年輕人,也有幾個村長幫的人,他們原來早就埋伏在漆黑的樹林中。剛才的森普斯和村長的對話,他們通通都聽到了。他們的臉上充滿鄙視和憎惡,恨不得將村長碎屍萬段似地。
村長全身發抖,近乎抽搐。他坐在地上,手指著森普斯,眼則望著安貝羅:「你們陷害我!這是個陰謀!你們陷害我!我只不過是懲罰有罪的人罷了!」
安貝羅冷笑道:「我們陷害你?」他指著橋的方向:「那他們又怎樣?」
村長回頭望去,這才發現對岸已站滿了人。是那名婦人依照和森普斯之間的約定,把村民都通通帶來了。先前村長只顧和森普斯對話,完全沒聽見人們的腳步聲。但現在才發現,已經太遲、太遲了。
他一躍而起,雙手按著頭,陷入狂亂般拚命嘶叫:「你們陷害我!這是個陰謀!你們陷害我!我只不過是懲罰有罪的人罷了!只不過是懲罰有罪的人罷了!」
森普斯那上薄下厚的嘴唇,冷冷地吐出一句:「別自欺欺人了。」
村長的動作忽然停了下來,也不再喊叫了。他望向森普斯,森普斯也看著他。但寂靜並沒有維持多久,他再次狂叫起來拔腿就跑。安貝羅等人想抓住他,但已經趕不及了。村長向橋直衝過去,但沒有踏上橋,而是往下跳進河裡。森普斯跑上前往下望去,剛好見到村長的手沉到河水之中。而凸出河面的一塊石頭上,則染上了一片詭異的顏色……眾人都圍上來,但沒有人說話。
當森普斯再次來到這條村時,已經是一年多後的事。橋已經建好很久了,對岸的橡樹林清掉了一片。變成一個小廣場,四周則是麵包店、雜貨店和各種工坊。原本的房子有些已經重建了,由一層高變成兩層高。不少旅人、商人經過此地,在此留宿還做些小買賣。森普斯以前住過的那家旅店也遷到了對岸,但掌櫃的仍舊是同一人。
森普斯坐在店裡最後一把椅子上,點了黑麥麵包和魚湯。吃完後,他便向掌櫃的說:「事情過了已經一年多,村長已經有人當了吧?」
掌櫃慌忙把手指放在嘴前,發出「噓」的一聲。見其他客人沒注意,才來到森普斯身邊耳語道:「別這麼大聲!還有別提死人啊意外啊甚麼的,會嚇跑客人的!」
森普斯聳了肩:「我沒有說啊!我只是問誰當村長了,是安貝羅嗎?
掌櫃的說:「怎會?他在各地的的生意都忙得很,所以就拒絕了邀請。」
這時,一把熟悉的聲音從樓梯那邊傳來了:「人不說話是不會死的,但不吃東西就會死了。」是安貝羅,他看起來還是老樣子。不論是容貌或神態,均一點也沒變。他踏下了樓梯,來到桌邊,拍了拍掌櫃的肩:「給他啤酒,我請。」
森普斯向他豎起了大姆指,安貝羅也微微遞起手表示會意。就是這樣,森普斯在橡林村——不,也許該叫橡林鎮,渡過了平靜和諧的一天。
(本章完)





-01.png)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