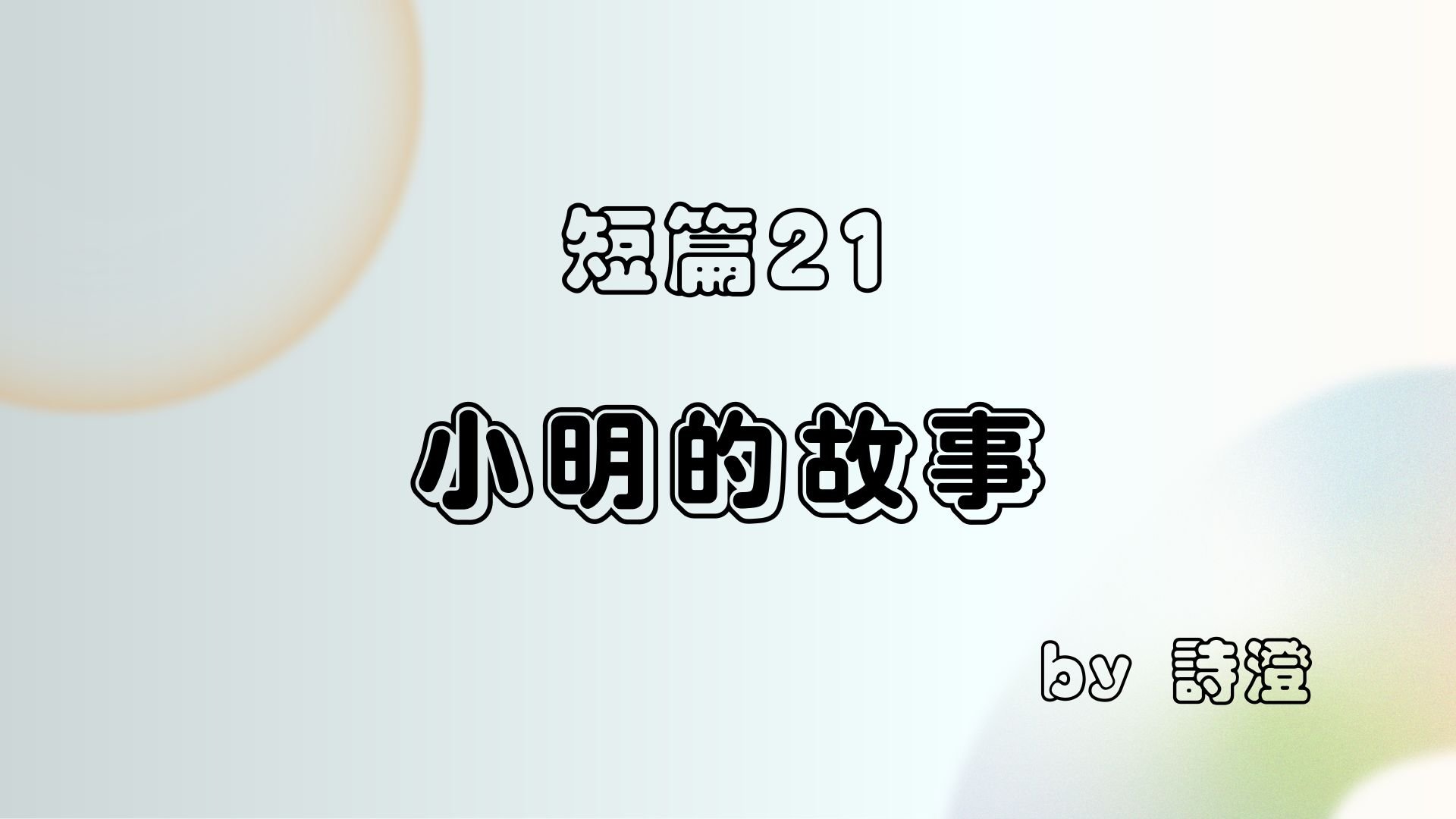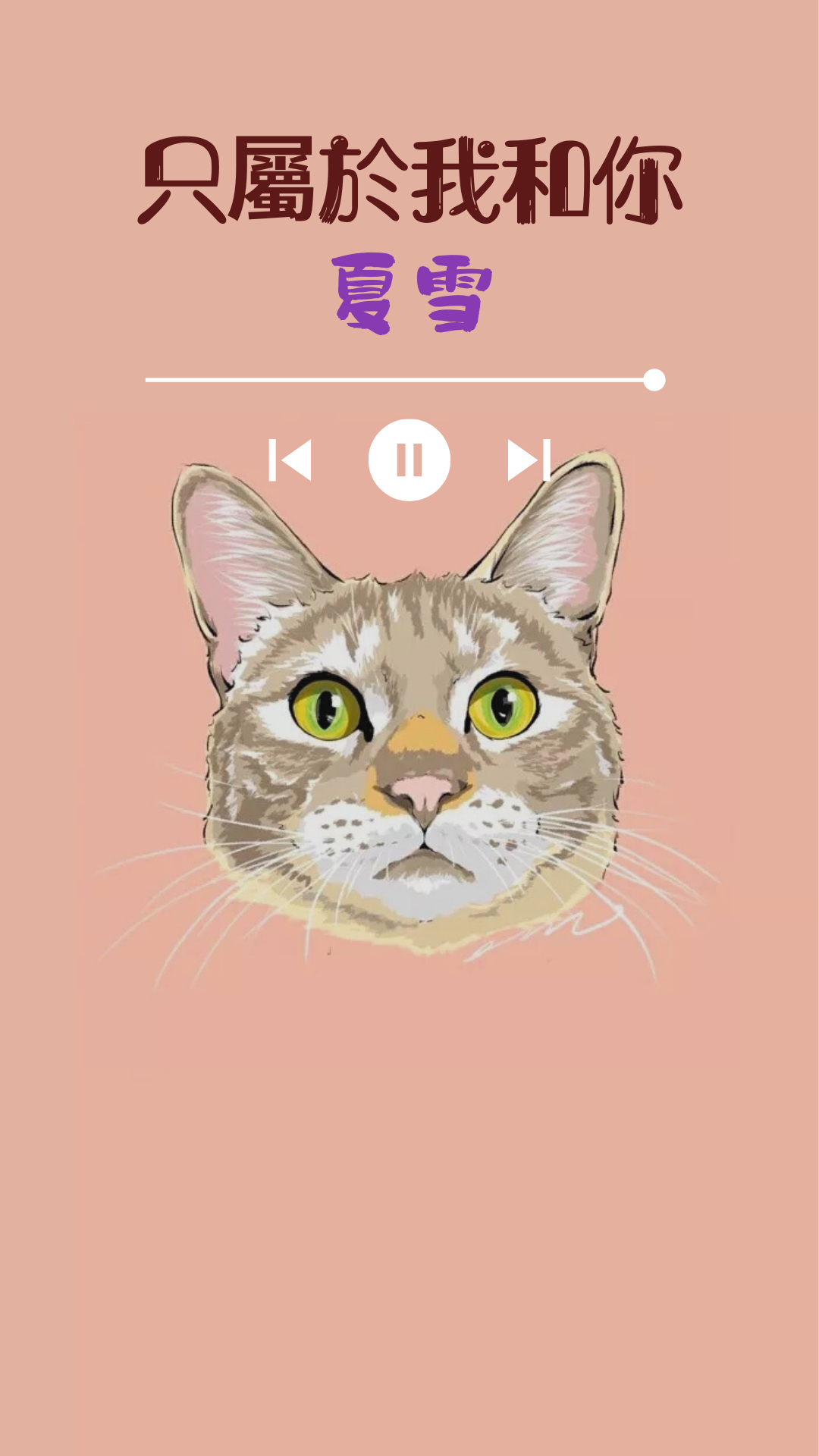「你別再妄想追求我的馬子,看一眼也不行,否則你就死定!」這是我在學校三樓男廁裡暈倒前最後一句聽到的話。我醒過來後摸摸自己的後腦,濕了一灘紅色且帶有腥味的液體,但確實是什麼?我不敢去猜。我突然覺得這個世界變得很奇怪,怎麼只有一條線的寬闊?這時我才知道我的一雙眼睛已腫脹得如雞蛋一樣大。我透過雞蛋的裂縫看一下手錶,玻璃錶面碎了,時針和分針不知身在何處,秒針卻還在轉動。雖然不知時間,但看窗外昏暗的天色,大概入夜了。街外橙黃色的燈光透過磨砂玻璃朦朧地照進來,把我的校服也照成黃色,我以為是這樣。我用衣領抹一下嘴角的傷口,強烈而噁心的尿臊味立即侵入我歪斜的鼻樑下面破損的鼻孔。原來不是燈光,我的校服「本來」就是黃色的。其實已不是第一次,不過這次多了點事端……
我每天上課前都會去學校裡面的小賣部吃早餐。這個習慣從年半前開始,正確來說,是從那天我坐在小賣部外的長椅上貼藥水膠布,碰上了她之後開始。我不知道她姓甚名誰,也不知道她讀幾年班,只知道她身穿的,是我一直認為是奇怪,醜陋的我校的校服。我還以為一輩子都無法找到一個女孩能把它穿得漂亮,但她確實出現了。也許不是她穿得好看,而是她根本就是「美麗」這個字詞符號真正代表的意思。我從未見過她,若非那套校服,我還以為有個美麗的天使被魔鬼擄入這所地獄裡的學校。她買完麵包邊吃邊讀報紙時,微微瞟了我一眼,然後又繼續讀報。隔了幾秒,突然抬起頭來正視我,跟我四目交投。我感覺到兩邊耳朵首先發熱,然後兩頰也跟著泛紅。我緊握著一盒藥水膠布,心想:「難道她發現我凝望了她很久?要怎麼辦呢?她該不會以為我是個變態吧……如果我很著跡地移開視線,就更無私顯見私。」在我不知所措的時候,她對我笑道:「你似乎傷得很重,阿明,用藥水膠布怎可以呢!」我頓時呆若木雞,腦子停止了轉動,大概是受到了極大的衝擊。當我的腦恢復運轉後,第一個想法是,住在梵蒂岡的教皇的電話是甚麼?我想我找到了神跡!她竟然知道我的名字,而且主動跟我說話!
自此,我每天都會來小賣部塗藥水和貼膠布,順便吃早餐,如果我的嘴巴還未腫脹得張不開的話。雖然她每天都和幾個女生一起吃早餐,我無法走近,但偶爾也會向我點頭打招呼。我把她當成我最有效的止痛藥。為什麼我每天都傷痕纍纍?因為我是學校的壞份子,我準時上學,準時交功課,每次測驗成績也不錯,而且尊師重道,原本。我這些破壞「規矩」的行為惹起所有同學的憤怒,就如在中世紀表演魔術一樣,我是異類,我是邪魔,我做了不應該做的事。因此我已經減少交功課,也沒有溫習課本,只有準時回學校,因為我要去小賣部。可是,「習慣」這種東西不是我想得這麼容易改的,他們習慣了每天給我強烈的痛楚刺激,並以傷痕作為我每天的開始。我曾經有想過究竟是我體格強健,而這麼能熬,還是因為他們的習慣使我變得這麼能熬。
圖書館是我最後的避難所,因為他們是不看書的,平常很少會來。連圖書館管理員也沒有,除了我之外。我早就習慣了這所學校的同學的模式,所有學生都是胖虎的樣子。打架和收保護費似乎是必修科,連女生都不例外,想到這裡我就覺得很奇怪,經過我明查暗訪才認識的那位美麗的她,究竟過的是怎樣的日子?看來又不覺她被人欺負,真是奇怪,不過有些事無謂想得太多。反正我也要在圖書館待一段時間,隨便打開一本小說,消磨一番。故事是說一個英雄人物的冒險事跡。主角排除萬難,練就一身好武功,把歹角一一打敗,成功抱得美人歸。這種故事一年到晚都不知出版多少個,現實哪有這種英雄呢?「誰說沒有?只要你想,你就是。」突然有道聲音不知從哪裡鑽出來。雖然我知圖書館裡沒有他人,但我沒有覺得驚訝,因為出現幻覺也不是第一次,大概就是腦震盪比較多而導致的。
「別小看你自己,你只是未發揮出潛能而已。」神秘聲音又來。我沒有理會,繼續看書。「怎麼?好歹你也給我反應好不好?」他繼續道。我只好合上書本,把它放回書架上。「合上書本也沒用的,我不是藏在書裡,我是藏在你的心裡。」他仍不打算放過我。我沒好氣地回答:「那你想我怎樣?書,我是讀不成的;人,我是打不過的;女,我也是追不到的。」他回答:「我來幫你。」
雖然剛剛三時半時被同學練習了空手道一會兒,但我還是趕得及四時去到三樓廁所外面。她已經到了。我拖著伸不直的腿,以我最快的速度走上前,打個招呼。她仍是笑容可掬,可愛動人的樣子。她對我笑說:「怎麼從未見過你沒有受傷的樣子?傷得這麼重就別辛苦走過來了,去看醫生吧。」我當然是故作瀟灑:「這一點兒的傷,算是什麼?我一點都不放在眼內。對,你找我有什麼事?」她緊緊扶著我,其實我被扶得很痛,但我絕不可能撇開她的手,而且忍痛本來就是我的強項。她輕輕在我瘀紅的瞼上吻了一下,然後說已留意我很久了,很喜歡我,請我也吻她一下。噢!我肯定在走「狗屎運」!我猶疑了二點三三秒,我吻下去......啪!她狠狠摑了我一巴掌,然後跑到放學很久,但竟還未離去而「剛好路過」的胖虎身邊,挽住他粗大強勁的臂彎。我遲疑了幾秒,開始明白到我不是走「狗屎運」,而是將要吃「狗屎」。
我知道解釋是一個最不理智的做法,而且我解釋不了;我知道既然是局,一定有很多人埋伏,回頭一看,果然很多打手;但我不知道她為什麼要這樣做,難道我每天在小賣部遙遠地凝望她,使她很討厭我?還是說她根本就不是天使,而是比撒旦更邪惡的魔鬼!「還擊吧!這是你揚名立萬的好時機,打倒了這幫人,你以後就不會再被人欺負了!」書神又出現在我的耳朵裡。我大喊:「神經病!打你個頭!」胖虎和嘍囉眾人當然以為我是跟他們說的,呆了一呆,然後捧腹大笑,連她也笑得合不朧嘴,那種笑聲完全就是電視劇裡,奸角做完壞事得逞時的笑聲。我終於爆發了,猛然撲向其中一個嘍囉,給他吃了一個右勾拳。他反應不及跌倒在地,吐出一隻蛀牙和幾滴血水。其他人先是驚訝,然後一湧而上。我再使出側踢和直拳,把兩個嘍囉重擊倒地……
到現在我還記得暈倒前的那麼多的事,證明我的腦袋沒有大礙。不過身上的尿臭味的確比較難忍,我慢慢解開校服的鈕扣並脫去,步履蹣跚地爬到洗手盆,扭開水龍頭,用軟弱無力的手盛著一點水向滿佈傷口的身上澆。「你現在……」書神又想說話,不過我輕輕搖擺腦袋,他又消失了。而我從染紅了而且破裂的鏡中,看見一個腫脹瘀傷不似人形的鬼臉,擱在洗手盆上,嘴唇微微張合,卻沒有發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