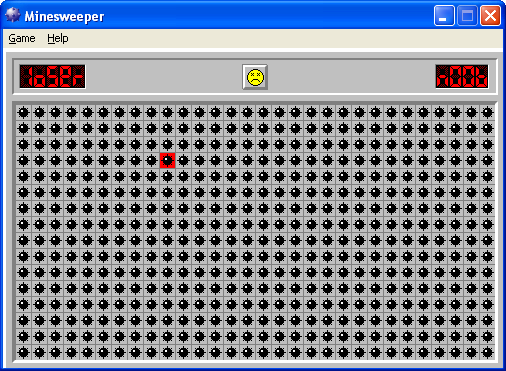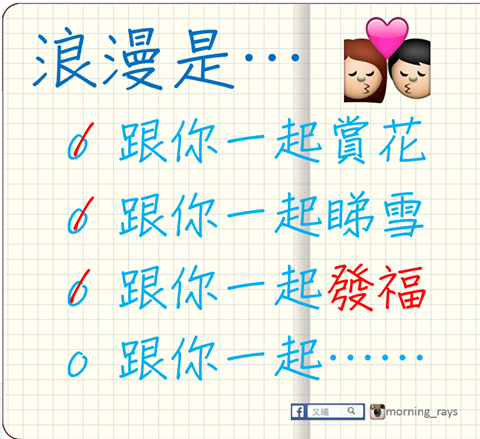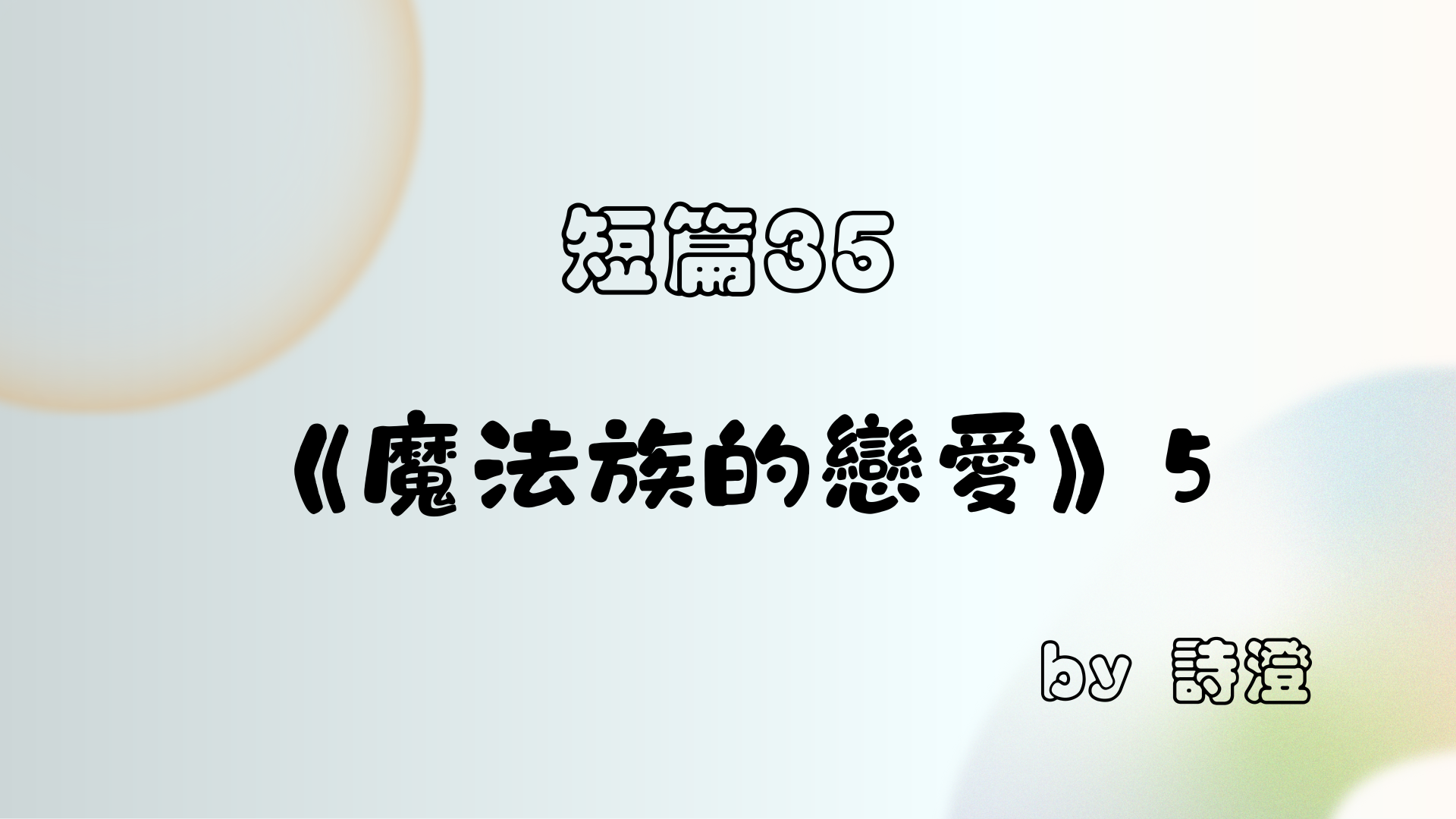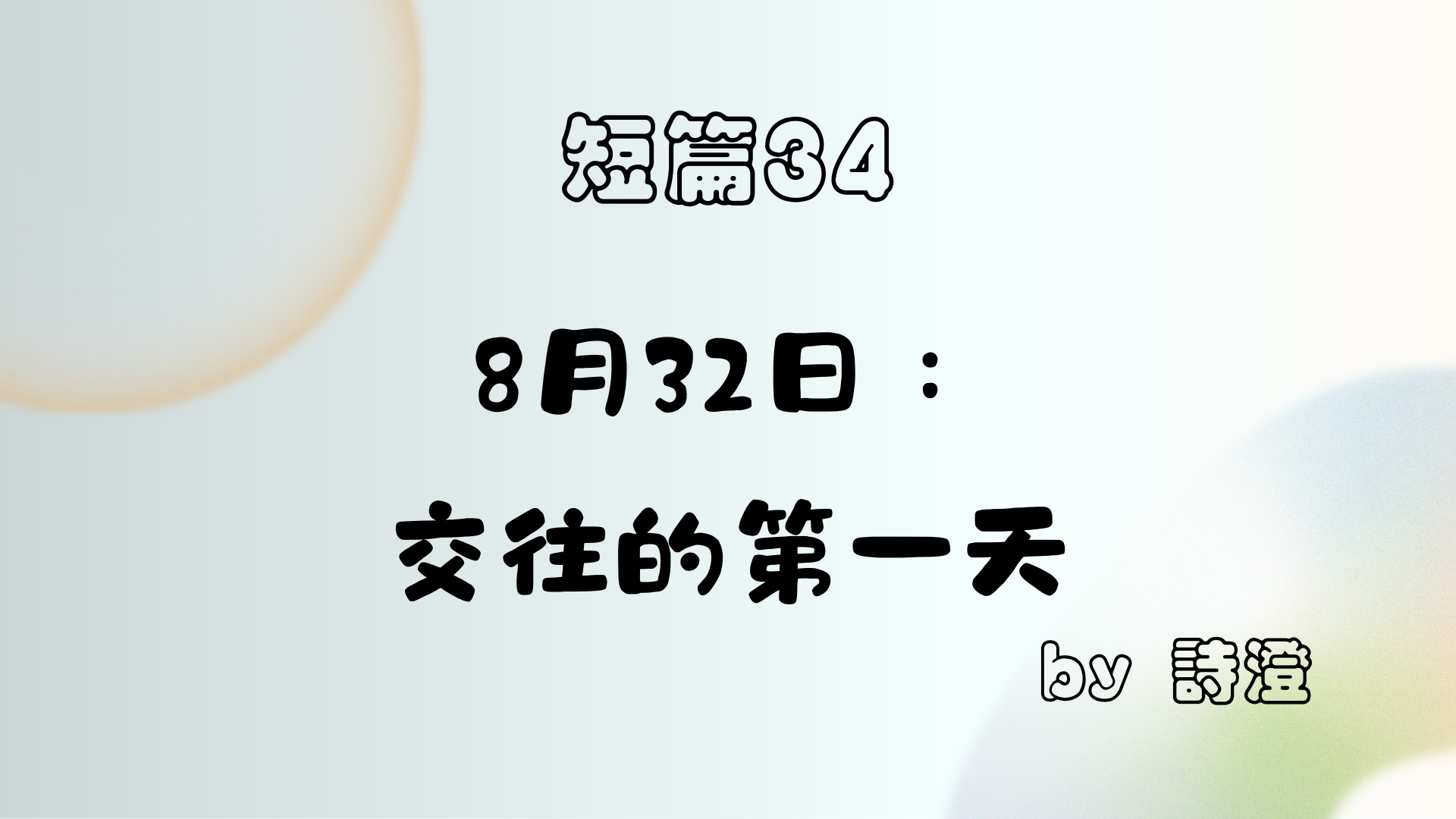<<調音師>>
1
爸爸不在場,我成為正式的調音師出外工作,這是第一次。城市內的空氣冰冷,天陰陰沉沉下着很大的雨。
爸爸是一位有三十年經驗的樂器調音師,主要的工作是為鋼琴調音及維修。在我讀大學的時候,爸爸會間中叫我幫忙,大概是因為覺得讀大學的我很閒。不過與其說是幫忙,倒不如說是做苦力,我雖然會彈鋼琴,但為鋼琴調音我是不懂的。爸爸年紀雖大,頭髮半灰白,但耳朵很靈,其實不需要別人幫忙,當要移動鋼琴板的時候,我才派上用場。
記得有一次,爸爸對一個客人說:「你的鋼琴如果要修理會很費工夫,共嗚板因為潮濕發霉,有幾個琴鍵沒有了,線壞掉太多,踏板機械也救不了。」客人說他其實本想扔掉那部琴,但還是抱着不想「把琴浪費掉」的想法,請爸爸來修整。
那一次我們三個人合力將鋼琴抬到垃圾站,真的累昏了頭。
客人給的錢,是作為答謝的搬運費,便打發我們走。爸爸說一個不想把琴浪費掉的人,怎可能將鋼琴弄得如此體無完膚,一點都不懂得珍惜。
他把鋼琴內一份發黄的文件拿走,那是鋼琴的出世紙。我們家裡有不少這樣的文件,爸爸都會珍而重之的收好。他說自已是收集死亡證書,心中對它們感到哀傷。我記得那是一部YAMAHA,生產年份記不清楚,大概也不是出廠了很多年,真是浪費。
到了後來我明白爸爸需要的並不是我的勞力,因為他常帶着一個大木箱,木箱上了鎖,非常的重,可是他從來不讓我替他拿。
爸爸在工作時會自言自語,說他的工具箱內有甚麽,叫我替他拿,又會解釋現在正在調整些甚麼。簡單的情況就是調整音準,弦槌、擊弦、踏板機械包括頂桿和踏板等。他會解釋鍵盤和整個擊弦裝置的運作,幸好我懂一點鋼琴,否則是一頭霧水。
路旁的一輛平治駛過水窪,雨水飛濺到我的身上來,使我大衣濕透。其實雨下得這樣大,就是橕了傘也沒多大作用,而我拿的是縮骨遮,更顯得無能為力。褲管早已濕透,濕和乾的部份成了兩截顏色,身上濺了酸酸的雨水,整個人狼狽不堪。這城市的雨水總是灰色而且是酸的。
現在感覺是打着八號風球的風和下着紅雨的雨,但是天文台沒有掛八號風球或是紅雨。我叫了聲慘,呼氣的暖氣使水份凝固成霧,真的很冰。看一看智能手機上的時間,六點半左右,難怪街上滿是趕路歸家的上班族。
我戴著入耳式的耳機,放着古典音樂德布西的鋼琴曲《映像》,看着打在街道上的雨水,鋼琴聲清澈得如流水一般,感受着像是身處晶瑩透明的水中的同時,鋼琴聲忽然變細,手機的短訊「鈴」一聲響起。
敏:「外面雨很大,小心點。」
我:「妳應該下班了,妳有帶傘嗎?」
敏:「沒有,你給我帶過來。」
我:「真的?可是我正在趕過去……」
敏:「說笑罷了。」
我:「我很想妳,明天可以見面嗎?」
這時德布西的意象再變得大聲,她沒有即時回覆,可能正在離開公司的途中。德布西真的是一個天才,正在彈德布西的鋼琴家也很厲害,說起來德布西的曲子大多都很難彈,手指的技巧要求很高,要花好一段時間練習。我沒有厲害到能彈德布西,練習倒也是嘗試過的。
爸爸有時會聽我練習鋼琴,他說:「聽上去很厲害,是德布西嗎?」
我說:「是的。」
爸爸說:「能彈德布西算是很厲害,可是你可別自滿啊,有人說偉大的鋼琴家霍羅威茨在老年時說,自己也是剛懂少許鋼琴而已。」
以前的人不像我們一樣,學每樣東西都要上課,上興趣班,找專人來訓練的。他們沒有那樣的機會,沒有那樣的時間,沒有那樣的錢。爸爸不懂彈很高技巧的蕭邦、李斯特、德布西,可是他的鋼琴也很厲害,巴哈有名的奏鳴曲、柴可夫斯基的船歌等,他都會彈。
他說有名的曲子,很多人會聽得懂,會有共鳴的,難彈的曲子會令人覺得厲害,不過一般人都聽不懂。
我走過了滿是行人的街道,來到客人的住宅。它是一棟有會所的高尚私人住宅,一個單位就要上千萬。我有少許被這氣勢壓倒,畢竟我家境不好,剛畢業就失業。我收起了我的縮骨遮,管理員向我這邊看過來,問:「年青人,到哪個單位?」他的話有一些鄉音。
「814A。姓張的。」
「來做甚麼的?」
我將縮骨遮放到自己的背包,好不狼狽,將修琴的大木箱提高了少許,這時再次感受那木箱有多沉重,笑了笑:「來修理鋼琴的。」
「噢,小師傅。」
我走過電子玻璃門,說了謝謝,進到一個堂而皇之的大堂,這裡打掃得一塵不染,等升降機的地方,竟然這麼寬敞。這位客人很富有,據爸爸說夫婦都是醫生。
「他們人很好,鋼琴保養也做得不錯,很容易調,既然而已答應了人,就不好爽約。今次你自己去吧。」爸爸躺在病牀上,以一副在我看來不大負責任的感覺說。
管理員在不遠處呼喚:「坐升降機到公用平台,要走到8座去,然後再坐升降機到14樓。」我按了升降機的掣數遍,似乎那樣按它會來得快一點。
和我在同一部升降機的住客都悠然自得,眼晴很醒目,看着就覺得很能幹的樣子。公用平台有花有草,根本是一個公園,可是沒有甚麼人使用這個粉飾得美輪美奐的地方。走到8座去,又有一個管理員,仍是很好的禮貌,說這年頭很少看到修理鋼琴的,說來裝修的見很多,又說天氣真的很冷,只有十度左右還下大雨。
我拿出智能手機,看了看時間又重新看了一遍客人的地址,坐升降機來到14樓,找到了A室。在門外可以聽到小男孩玩耍的叫聲。我按下了門鈴,站在門外等候,不一會兒,門打開了,一個女人站在那裡。
她丈夫是姓張的,所以她應該也叫張醫生。只不過當時我的腦袋並沒有立即想到這些,因為她真的很美麗。她大概二十八、九歲,看上去很高,也許是因為她的優雅而令我覺得自己好像變矮了吧?其實應該只有一米六左右,身上穿着一件奶白色的薄紗外衣,外面天氣很冷更加顯得她的衣服單薄,沉藍色的綿質長褲,赤着足踝,身材很好而且膚色亮白透紅,和外衣融為一體。烏黑的長髮及肩,沒有特別的整理也顯得很合適。臉蛋很尖而且很有光澤,好像剛剛做完面膜一樣,眼目清透,只不過精神有點累。
「啊,張醫生妳好,我是來修理鋼琴的。」說出這話是在見到她的兩秒後。
她說:「噢,你好,請進來吧。」我聽到屋內有小男孩的叫聲:「媽,是誰?」
我將濕透的運動鞋脫掉,剛踏進屋內的光潔地板,立即感到很尷尬,因為雨水的緣故,就連袜子也濕透變色,在地板上留下了一個水腳印。她不好意思地說:「噢,外面雨很大哩,你脫掉袜子吧,我拿毛巾給你。」聲音很温柔。
我就在門邊脫掉袜子,有夠尷尬的赤腳站了一會兒,腳很冰冷,這時我發覺原來屋內有暖氣。
她回來時遞了毛巾和布拖鞋,粉色的毛巾有簡單的花紋。我放下大木箱,稍為弄乾了腳,就提起大箱走進了屋內。
她的家很寬敞,裝修很簡單,米色的牆身、米色的天花、米色的燈光。沒有甚麼亂放的東西,整齊得很。
她說:「你是本嗎?你爸爸在電話裡提起過你今天會來。天氣那麽壞還讓你來真不好意思。」
我說:「不用。」
她說:「對了,張醫生是我丈夫的稱呼,你叫我艾娜好了。」
我說:「好的。」
有了屋內的暖氣,身子開始暖和起來了。
這時有個小男孩跑過來叫着:「媽,是誰?」小男孩大概三、四歲左右,很活潑的樣子,和艾娜有七分相似。艾娜曲身抱着小男孩,之後看着他的臉說:「哈哈,叫本哥哥吧,是來修理鋼琴的。」小男孩的乳名是「哈哈」。
哈哈說:「為甚麽,要修理?」他年紀少,話不是說得很好。
艾娜說:「因為鋼琴音不準的話,彈起上來會很難聽的。」
哈哈說:「媽媽你很少彈呀。」
艾娜說:「對呀,哈哈現在彈得比媽媽好。」
哈哈說:「我彈的時候包包會跑掉的。」他用他很小的手指指向窗台,那裡有一只短毛肥花猫,花猫正捲成一團睡着,可以看到牠的肚子一起一伏的。
艾娜說:「你要多練習,包包才會聽的。」
哈哈跑到包包身邊,仲手順着毛的方向撫摸下去,包包的眼睛睜開了一半,就又閉上眼睡覺。
哈哈忽然看向我這邊,然後又回頭對艾娜說:「媽媽,肚餓。」
艾娜笑着說:「要等本哥哥調好了琴,我們再吃飯好嗎?現在回房玩吧。」
哈哈又對艾娜說:「媽媽,肚餓。」不過還是回自已房間去了。
艾娜擺出苦笑說:「孩子就這樣。對了,你要喝點甚麼嗎?」
我說:「不用了。」頓了一下,「可是有孩子很幸福吧?」
艾娜說:「對啊。」然後打量了我身上的大衣,說:「外套我替你放好?」
我說了謝謝,將外套脫掉,她接過之後帶我到一個房間,打開了房燈,是一個書房吧?有簡單的傢俬,書桌上擺了很多文件,有兩部手提電腦,都是實用型的。書架上有很多書,我想醫書約有幾十本,解剖學、病理學、藥理學、微主物學、外科手術等,其他都是文件。
書架旁有一部直身鋼琴,有深紅色的布蓋着,上面放了幾份琴譜,有打印的也有原譜,琴腳附近有兩三箱雜物,雖然鋼琴似乎是有間中使用,不過艾娜自己應該很少彈吧?
艾娜將琴譜放到書卓上,又將鋼琴上的布挪開,之後我幫忙將琴腳附近的雜物箱移到房的一角,其中一箱搬的時候有一些金屬碰撞的聲音,艾娜聽到後,顯得有些慌忙,走過來說:「都是些不要緊的東西,讓我拿吧。」
不過紙皮箱是半敞開的,我看了一眼,裡面都是音樂比賽的獎狀和獎杯。
我接着和她一起將鋼琴上下門和頂蓋移開,她好像顯得有點吃力的樣子,上下門放到一旁,可能因為搬動聲響,哈哈從另一間房走來,依偎在門旁,一臉興致勃勃。艾娜笑着說:「上一次調音是你爸爸調的,好像有一兩年了吧?」她的笑容很美麗。
我說:「是嗎?」爸爸說艾娜每一年大概這個時候都會請他上來調音。
艾娜說:「你爸爸怎麼了?身體不舒服嗎?」
我說:「對,病倒了。」
艾娜說:「要保重身體啊,病的時候可以看我。」
我說:「對啊。」
艾娜說:「你會調音很了得嘛。」
我說:「只是跟爸爸學了一點點,妳是我的第一個客人。」
艾娜說:「真的?我很高興!」艾娜的表情很真心,很難認為她是在說客氣話。
我說:「我不知做得好不好。」我有點兒尷尬。
艾娜說:「放心好了,你是剛畢業?」
我說:「我早畢業了,打過一會兒工,可是沒過多久就辭工了。」
她停了一下子,說:「可能你爸爸想你繼承衣缽?」
我說:「也許吧?反正我不喜歡坐辨工室的工作。」
想起來爸爸煞有介事的帶讀大學的我去為鋼琴調音,可能是想分享當中的樂趣和要我繼承下去。人年紀大了看事情都很不一樣,和壯年不同,因為每天也覺得自己活不長,就滿腦想着下一輩的事,想將最好的留下來。人過身了,甚麼也帶不走,正如人出生,甚麼也沒帶來。假如人不留點甚麼給下一輩的,就好像沒有活過一般。
艾娜打斷我的沉思似的,說:「好了,我不礙着你調音,我要把佣人姐姐的飯餸煮了給哈哈吃。」
我說:「好的。」
艾娜走到房門口,對哈哈說:「好啦,我們不要礙着哥哥吧。」接着拖着哈哈走了,哈哈好像還是很感興趣,走的時候目光是看着這邊的。
房內只有我一個人,這時才留意到書卓上幾幅的全家合照,有夫婦的結婚照,也有抱着嬰兒時的哈哈的照片。張醫生年紀應該比艾娜大幾歲,看上去很高大健碩,皮膚曬得黑黑的,像是經常運動,笑的時候瞇起了眼咧開嘴,很幸福的模樣。
這時手機震了一下,是短訊。
敏:「可以呀。」
我:「幾時見面?明天晚上?我到了客人家了。」我習慣了甚麼事都讓她作主,有時候她會說我太沒主見,不過讓她作主好像所有的事都會順利一點。
敏:「我正在回家,很很很大雨!」之後她傳了一張雨景的相給我。
我:「妳應該照自己給我看,敏。」
敏:「明天晚上可以啊!工作加油!」
我打開了爸爸的工具箱,工具大概都認得,調音扳手、吉布頭、止音橡皮、音叉、調音器等一應俱全。
艾娜的直身鋼琴是Sauter,德國品牌,比Steinway少點名氣,可是是很好的鋼琴,音色清脆悅耳,要沉穩時低音也很穩重,鍵比較硬,比日本琴難彈。我簡單彈了幾個高音,音色音準並無大偏差,鋼琴保養得接近八成新,這樣的鋼琴彈出來比全新的琴還要好,音色沉實老練一點。
我老實不容氣的坐下彈了一小段蕭邦圓舞曲,之後開始由中間的音向高調起,每一個音都用力彈上十多次,每一個音都調,爸爸也是這樣。最高的音好像失準得比較嚴重,然後調低音,有一個E鍵的弦有些奇怪,怎調也調不好。
這時哈哈走了進來,好奇的問:「哥哥在做甚麼?」
我說:「調音呀。」
哈哈說:「哥哥會彈嗎?」
我說:「一般吧。哈哈肚餓嗎?」
哈哈說:「肚餓。」
我說:「你會彈甚麼?」
哈哈說:「普通的。」
哈哈拿起了扳手把玩,當成了搥仔,很高興。
哈哈說:「會彈甚麼?」
我說:「很普通的。」
之後他問了我很多問題,主要是關於琴的內部,因為很少看到,又問了爸爸的工具箱內的事物。
我說按鍵的時候,住在鋼琴內的小矮人會高舉槌子,打在弦線上,就會有聲音。如果不和小矮人好好說話合作的話,小矮人不工作鋼琴就不發聲了。他似乎很感興趣,試着彈了幾下,要看看有沒有小矮人跑出來。
艾娜的晚飯好像做好了,從客廳傳來陣陣香氣,聽到艾娜叫了聲:「哈哈,吃飯了!」
哈哈「噢」的一聲,走了出去。我覺得他長大後應該會很聰明伶俐。
和哈哈玩耍的時候不斷的調低音E,哈哈出去的時候弦線竟然叮一聲的斷了。
我赫了一跳,趕忙看看木箱內的鋼弦架內,很不巧竟然都沒有合適的。
艾娜聽到聲響走了進來,問:「怎麼了?」
我很慌張,說:「弦線斷掉了,可是我碰巧沒有合適的替換。」
艾娜說:「沒有辦法?」
我連忙打了一通電話給爸爸,他說線剛好用完,新的買了放在家中,可是還沒放到鋼弦架,自己就病倒住院了,忘記了對我說。爸爸說:「對不起,本。實在沒有甚麼辦法,你修一下踏板機械,下一次再上去吧。」
我對艾娜解釋了一下,說:「真的很對不起。」
她說:「既然這樣也沒有辦法,可是下一次要兩星期後,因為我總是要當值,不是很經常能夠像今天早回家。」
我說:「對不起,只好這樣了。」
她說:「兩星期後好嗎?」
我說:「好。」我看了一下sauter鋼琴的踏板機械,忽然好奇的問:「那麼平常是誰在照顧哈哈呢?」
她說:「佣人姐姐,因為我都很早上醫院工作,而且很晚回家。」
雖然覺得不好意思,可是我還是隨意的問了一下:「妳先生呢?」
她稍為停頓了一下,說:「他…應該是在工作吧?」
我說:「噢。」我繼續檢查踏板機械,三個並排的踏板,最右是常用的延音踏板,和一般鋼琴一樣,因為常用的原固,前端金色的表層已被磨得光滑,有點生銹。中間的消音踏板出奇的有使用的痕迹,因為這踏板很少用,一塊绒布會被降下在琴槌和琴弦之間,使音變得細和模糊。
最左的柔音踏板也有明顯的使用痕迹,在直立式的鋼琴中,踏下柔音踏板使琴槌移近琴弦,使琴槌擊力減低。
爸爸曾經說,只是看一下樂器,就大概知道使用樂器的人的習慣和性格。
我說:「妳有彈拉威爾或是德布西嗎?」
她說:「一兩首是會的,不過很生疏了。」
和艾娜對話的時候,不知為甚麽感覺很空洞的,就像拚圖拚了大半,卻發現少了幾塊的那種失落的感覺,只看其他部份是很美滿,只不過缺了塊的拚圖就是不夠完美,成不了一個圖畫。
我猜她彈琴都是在晚上彈,在放下了绒布消音的情況下彈。
我修裡好了踏板機械,就大工告成了。花了整整一個小時,可惜修不了那個E的弦。這時我坐下了,然後開始彈一首蕭邦圓舞曲。音色很清脆,旋律叫人起舞。爸爸習慣上都會在調音後彈一下,說要聽聽音準和效果如何。我覺得根本聽不出來,只是想過癮而已,反正我自已都很少彈到這麼名貴的sauter鋼琴。
艾娜進來說:「哥哥很厲害嘛,哈哈你說對不對?」
我站起身來,說:「好了,妳來試一下好嗎?」
哈哈爬了上琴櫈上,亂彈了幾下,艾娜在他身旁坐下,笑說:「你認真彈嘛。」
艾娜接着彈了半首德布西的《映像》,起初彈是半玩耍的,節奏也沒有以一般演奏的速度,比演奏時快得多,有時候又太慢。過了頭一分鐘左右,她認真的彈了中間的部份,表情也變不同了,美麗的身體有了律動,奶白色的薄紗外衣就隨旋律舞動一樣。不知是真的生疏了,還是因為哈哈坐在旁邊擋住了高音部份,有很多的錯音。
爸爸說,當調音師最大的滿足感是能夠看到樂器主人重新彈奏樂器時的那種喜悅。看着他們的表情,就像再一次找到令自己滿足快樂的事一樣,全情投入演奏。看到艾娜彈奏的表情,我覺得她好像在尋找拚圖內缺少的一塊般,既淒美又絕望。
城市人有很多抑鬱的人,他們不能享受以前能令他享受的事物,對很多事物生膩,總是高興不起來。日復一日的平庸生活,沒完沒了的工作,愈多的事情不受我們控制。這樣說來,我們所有人都得了不同程度的抑鬱。
這時肥花猫懶洋洋的走來,是叫「包包」肥花猫。牠走進了房內「喵」的叫了幾聲,雙手拉得長長的伸了個懶腰,坐了下來。哈哈見到了牠,叫了兩聲「包包」,可是肥花猫並沒有理會,聽了一陣子音樂,似乎沒有人要給牠添猫糧,牠又悶悶地走了出去。
艾娜彈的時候真的有太多的錯音,我心裡有種悶悶不樂,因為艾娜很厲害,手指的靈巧技術,手臂向外的動作,身體隨音樂的律動,是一幅美麗的景象。她控制不了音量,我猜是因為艾娜已經很久沒有在拿掉消音绒布的情況下演奏了。
因為右手手臂常要避過哈哈的腦袋,艾娜自己也發覺彈不下去,突然間就停下了琴聲,房間回到寂靜,空氣静止僵硬,頭腦忽然被帶到現實世界。
艾娜說:「真的很久沒彈了。」
我說:「音準可以嗎?」
艾娜笑得很燦爛:「非常好啊!」
我說:「那麽我要走了。」
艾娜忽然由演奏家變成主婦,說:「謝謝你。本,你真的不要喝點甚麼嗎?」她站起身來。
我說:「不用了,我渴的話,下一次會向妳要一罐汽水。」
艾娜笑着說:「好啊!」
我收拾了調音的工具,鎖上木箱,和艾娜合力將物件還原。
艾娜拿了外套給我,我看一看窗外,大雨停了,可是天變得更黑。
艾娜替我打開門,說:「那麼下星期再見吧?」
艾娜真的很會照顧人,親切得有點嚇人,她說:「袜子就用我先生的吧。」她替我找了一雙綿袜子,灰黑色的男裝綿袜,很像那個醫生先生會穿的。我禮貌的推卻,可是艾娜堅持之下,我只好臉紅紅的穿上。綿袜有點兒太大,最前端還有空位。
我將發臭的袜子放進背包,自己也覺得噁心,可是沒有辦法。然後我穿上運動鞋的時候,哈哈從不知那個房間跑了出來,對我說再見。
艾娜也說了聲再見,就關上門。
我從背包取出耳機,戴到耳窩內,另一端插在手機上,打開手機,原來有好幾個短訊。
敏:「明天晚上吃晚飯嗎?」
敏:「還是有甚麼節目?你想吃甚麼?」
敏:「為甚麼不回覆?肥本。」
敏:「對了,最近總感覺有點奇怪,回家的路上有點不安,可能是錯覺。」
敏:「我到家了。」
有兩則短訊是朋友發來的。
雲哥:「明晚有空?」
秀:「你知道雲哥的事嗎?很爆笑的。」
升降機到了公用平台,我和管理員交換了個眼神。
我回覆敏:「剛才很蠢,弄斷了一條弦。
「明晚吃壽司好嗎?我可以來接妳。
「今天工作順利嗎?」
我按下了公用平台到地面的升降機掣。
我回覆雲哥:「明晚有約。」
我回覆秀:「甚麼事?一定很好笑,哈哈!」
公用平台到地面的升降機也到了,我進到升降機內,又失去了訊號。我按下音樂,德布西繼續響起,我改為聽美國流行音樂,因為我習慣了上班時聽陰沉失意,淒美一點的音樂,作為自我可憐,回家的時聽輕快一點的美國流行音樂,這樣心情會好一點。原則上我沒有不聽的音樂,只要合心意就好了。
敏:「肥本真笨。吃壽司好呀。」
雲哥:「那遲下再約。」
有一個6字頭的電話號碼:「現在手機有……優惠……」我沒看下去。
有一另個6字頭的電話號碼:「謝謝,現在音色很好。」
原來艾娜有我的電話號碼,應該是我爸給她的。
我將她的電話號碼加進了連絡人,名字改為「艾娜」。
我回覆:「斷了的弦,對不起,下次再修。」
艾娜:「本,你是周杰倫嗎?」
2
第二天晚上,我到了女朋友公司大廈的大堂等她放工。我比約定的時間早了不少,有些上班族下班的時候向我投以奇怪的目光。其實可能只是多看一眼,不過我已經怪不自在的了,在這種商業大廈以這種街頭打扮的男人也許不多。而且一看就知道我正在等人。
大廈樓高數十層,地下大堂少說也有層高的樓底,全直立式玻璃窗,冬天的陽光猛地照射進來,想不到昨天還是八號風球加上紅雨的雨勢,今天天氣竟然這樣好。
我玩了一會兒手機,女朋友忽然就出現在乘升降機下班的人群當中。
她穿着厚身的洋式淺藍色外套,窄腳長褲加上白色女裝鞋,在走人群當中,她的顏色是彩色的,明艷動人。
敏笑着走過來,我也笑着迎接她,她揮手打招呼,似乎見到我就是一天最高興的事。
我想抱她,可是她將我推開,說:「哈哈,人很多。」
接着我和她走出了大厦大堂,我笑着說:「為甚麼遲到了?」
敏說:「我哪有?你每次都遲到哩,還好意思說。」
我說:「我等很久了,妳怎麼補償?」
敏說:「補償甚麼?你不是很閒嗎?」
我說:「我們去哪裡?妳想吃甚麽?」
敏說:「壽司吧?你不是說想吃壽司嗎?」
我說:「好啊,工作順利嗎?」
敏說:「還不是一樣。」她看一下我的打扮,「你穿得很好看啊。」
其實我還不是和平常一樣,我說:「妳也很好看。」
敏說:「聖誕節有很多好看的燈飾,遲下去看嗎?」
我說:「好啊。」
她想起昨天的短訊,說:「你真笨,弄壞了人家的琴。」
我滿尷尬地手抓了抓頭,說:「本來就壞嘛。」
敏說:「那怎麽辦?」
我說:「再上去一次啊。」
敏說:「這次能弄好吧?」
我還滿自信地說:「當然了。」
我們平常的對話,手自然地拖着,敏的額讓我親了一下。
夜晚到了一家常去的壽司店,是一個人不會進去的那種店。壽司很好吃,味道很鮮。我和她本來就喜歡吃,而且和她一起的話,甚麼都變得很美味,是那種氣氛讓食物美味起來。
對我來說,街上大部份人顏色是灰色的,再漂亮的人也沒有留在我的記憶內,就像不曾出現過一樣。
我說:「明天到山上去好嗎?」
敏說:「噢,先前也說過了,決定到哪去了嗎?」
我說:「容易行的只有幾段路,我們先選一下?」
兩個人在一起很久了,行街睇戲食飯變得平凡,東西可以上網買,戲可以在家中兩個人看,接下來就只剩下日本壽司。
敏說:「好啊,我回家上網看看。」
我說:「嗯。」
我們吃過了晚飯,漫無目的的在時裝商店間穿來插去,她說這個好看嗎?那個好看嗎?我說都好看,不過我叫她試穿的她永遠也不會穿,縱使在我眼中她穿起來有多漂亮。她總是不相信我的眼光,反過來她會說讓我穿這個穿那個,然後帥的話買給我。
我們又到了化妝品店和便利店,都是必要逛的,就像遊客到著名景點觀光一樣,而且逛的時候漫無目的,甚麼都看;而我則是甚麼都拿起來然後放下來,其實甚麼都沒看,沒有興趣又沒有需要,跟着她像個傻瓜。
唯一的樂趣是固意擋在她身前不讓她看,這時她會左閃右避,還是看不到的話就會推開我說「別礙着!」
第二種樂趣是逗她的手臂、手心、肚子、頭髮。她的頭髮很好看也很香,雖然她經常更換洗頭水,可是我嗅到的是同一種芳香的香氣。她也很不喜歡在專注選擇貨品的時候被我騷擾,會很惱的說「不要搞我啦!」
第三種樂趣是為她提東西,因為這點小事我還可以為她做。
「唯一」的樂趣。
敏又買了新的洗頭水,她好像總是在買洗頭水。
敏說:「試一下這個牌子嘛。」
我說:「噢。」
我送她到車站,待她上車後,和她連連的揮手道別。
和她逛的街,是時間的延伸,正因為平常,感覺好像可以和她在一起很久很久似的。
車駛走了,我戴上了隔音很好的入耳式耳機,放了木結他的音樂,是很柔和的那一種。彈結他的那人是天才,我從十多歲就買了他的唱片,音色很優美,一聽難忘,我沒有想過木結他可以彈出這樣的音樂。
這時敏傳來短訊:「謝謝,今天見到你很高興。」
我:「我也是。回家路上小心。到了家給我發短訊。」
昨晚之後,我和艾娜互發了幾個短訊。
我回覆艾娜:「今天忙嗎?」
艾娜:「忙極了。哈哈睡不好,早上精神很差。」
我:「有上學嗎?」
艾娜:「我早上都讓他和鄰居的一個小孩上的士。佣人姐姐接放學。」
我:「要保重身體啊。」
艾娜:「我忙了,遲下再傾。」
我來到了車站,上了巴士,巴士電視在播一則新聞,說一個富商在兩個月前一場小提琴獨奏會中突然中風,入院治療了兩個月,反反覆覆最終不治死亡。報道指醫生也無能為力,之後說者訪問了好幾個有機會繼承遺產的親人,親人都表示哀痛。
我想看來一場爭產風波難免。
我回覆雲哥說:「下星期約出來好嗎?」
雲哥:「可以,『巨龍酒吧』?」
我:「好。」
從他回覆的速度看來,他也是一個閒得可以的傢伙。
我回覆秀說:「我約了雲哥見面,八掛一下他的事。」
秀沒有雲哥那麼閒,過了一會兒才回:「好的,那我們兩個人遲一點再約。」
這天是星期六,陽光明媚,不過可能因為有另一個颱風正在登陸,有一陣陣微風,可是風吹過來卻很舒服,一點也不覺得寒冷。
我準備了簡單的三文治,帶備了食水和毛巾等放在背包中,很簡便的出門了。和敏約好了在附近商場見面,我們倆都很準時,因為不想減少見面的時間。敏很精神,相比起平時收工時疲倦的樣子,更顯得漂亮。
敏知道我準備了三文治,表現得很高興,其實三文治只花了我半小時去弄,不過她已經很滿足,還和它們拍了張照片,說:「你以後也弄給我就好了。」
吃過午飯後,我們出發上山。往山上行,從山下看到經過人工修葺的草叢和植物,一直走到山上,取而代之的是高聳的樹木、亂中有序的野花野草和編編起舞的黃蝶。人變得越來越少,平地變得傾斜難行,石級斷斷續續。
忽然有一頭野猪從樹林裡探出頭來,把敏嚇個半死,她驚叫:「野豬呀!」
我從沒有見過活生生的野豬,因為是一個不折不扣的城市人。野猪有半個人的身高,只要牠衝過來撞一下或是咬一下,恐怕我們會受傷。
野豬並沒有衝過來的意思,牠只是呆呆的站在那裡,就在距離我們不到三米的樹林內。好罷,我們城市裡的人每天都做好迎接死亡的準備。可是野豬看起來顯得又笨又可愛。很久以前看過一本書,據說魔鬼梅菲斯特曾以獅子狗的形象出現在浮士德面前,如果能夠仔細觀察,看見野豬是否有一隻馬蹄足,就可以知道牠是不是魔鬼梅菲斯特,牠有著奇怪的稱呼:「蠅主、破壞者、說謊的妖精。」這些都是魔鬼的面相。
我們兩個人一口氣走了十幾級石級,回頭看時牠似乎已經不在了。
我說:「野豬很可愛呀!」
敏呼了口氣,說:「野豬會咬人的,你傻的嗎?」
我開玩笑說:「如果可以,我想跟牠做朋友!」
敏忍俊不禁,說:「真拿你沒法!」
我又說:「可惜沒有拍到牠,應該給牠照一幅相片!」
敏老沒好氣的說:「肥本!繼續走罷!真慶幸牠沒有攻擊我們。」
野豬是不是因為看到了敏所以沒有攻擊我們呢?我不知道,還是我在這現實世界有可以做的事?有別人要我做的事?當時的敏仍然很漂亮動人,可是她很怕野猪,似乎更害怕野豬傷害我。
敏走在前面,我跟在後面,路愈來愈難行,地上無數碎石使每一步腳掌落地時都角度不一。雖然如此,可是兩個人也不是特別的累,腳漸漸習慣了疲累時乳酸的作用,一步一步的向山頂進發。在途中是可以繞道不上山頂的,可是我們心想既然來了,當然要登上山頂。
和在山腳時不同,這時可以看到更多更遠的景色。我們現在身處比高樓大廈還高,感受着廣闊的空間,呼吸着自由的空氣。陽光在晴空照來,驅趕掉寒冷的空氣;放眼看去,可以看到一望無際的海洋。
敏說:「我喜歡看天和海連成一線。」
我說:「他們本來就是一體的。」
敏說:「這樣看的話,天和海的顏色是一樣的。時間就像是靜止一樣。」她深深的吸了口氣,然後幸福的笑了。
從最初和她在一起的時候,我希望時間就那樣靜止下來,那麼我們就不用在現實世界老去,然後因為死亡而永遠離別。
「時間就像是靜止一樣。」我重覆她的說話。
敏說:「本,你知道時間是多麼不確定的嗎?」
我說:「怎麼說呢?」
敏說:「你知道『現在』是甚麼?時間是流動的,沒有一刻可以叫做『現在』。」
我說:「『現在』不是『現在』?」
敏說:「這一秒是『現在』嗎?零點一秒是『現在』嗎?千分之一秒也不是『現在』。」
我在她面頰上吻了一下,其實我不太明白她在胡說些甚麼。
她笑着問我:「本,你覺得我們有將來嗎?」
我說:「當然有呀。」
「將來還沒有來,為甚麽你這麼確定?」她嘟着嘴說。
我說:「不然有甚麽?」
敏說:「誰知道你會不會跟別的女孩子發生甚麼?」
「可以發生甚麼?」我笑着說。
她輕輕扭了一下我的面頰:「還說可以發生甚麼?」
我忍着痛,頭左閃右避。她伸手又再扭了幾下,一邊扭一邊笑得燦爛。
我們任何一個都在追求一種永恆。不減的美貌、永恆的愛情、無盡的年歲、過多的錢財、太多的知識,其實我們連活得過下一秒也不確定。
我笑了一笑,說:「我說那個,是妳在網上看到的嗎?甚麼現在將來,怎麼像那些愛情分享網……」
敏說:「你別吵,跟我說『我永遠也愛妳』。」
我說:「我永遠也愛妳。」
我們接近山頂,風吹得比在山腳時強得多,強到可以將輕盈的敏吹走,我不時單手的扶抱着她柔軟的身體。
好不容易終於走到山頂,這裡比剛才的景緻更美更開揚,伸手似乎可以觸碰到蔚藍色的天空一般。
我們找到一片大石頭,在上面坐下並用手機拍照。
敏說:「你怎麼每一幅照片都一樣的笑容呢?」
我心想其實妳還不是一樣,不過我之後的幾幅相都手舞足蹈、擺出奇怪的表情、眼睛反白。可是相片的效果竟然出奇地好,看着那些相片,兩個人都大笑了。
我說:「說起來敏妳知道嗎,其實人都是活在記憶裡的。」
敏說:「我不知道呀?」
我說:「就像我是活在妳的記憶中一樣,也活在家人朋友的記憶中。」
「嗯。」她似乎在思考我的說話。
我接着說:「假如啊,只是假如啦,所有認識我的人都不在人世了,那麼有誰可以證明我活過呢?有誰可以說我曾經存在過呢?我就像不曾出現過嘛。」
敏說:「你可以留下一些甚麼呀。」
我說:「對啊,只可以說有些人活在別人的記憶特別久,不過最終都會消失的。」
敏說:「那麽說的話,假如世界的人都消失掉,這世界豈不是都會消失掉?」
敏說:「因為沒有人去證明世界存在過呀。」
「嗯。」我想了一下,我倒不曾這樣想過。
「不過呢,」她說:「這些都是假如的話。」
我說:「對了,我背包裡有美味的三文治呢!」
敏說:「對噢,走了這麼遠的路我也肚餓了。」
我從背包將放在保鮮盒內的三文治拿了出來,她很高興的和我分着吃了,看來她很肚餓的樣子。
太陽開始下山,為了在天色變暗前下山,我們倆趕緊收拾好行裝,沿路離開山頂。
下山時比上山輕鬆得多,不過因為山路陡玻難行,腳落下時擊力很大,所以下得山來雙腳都在發震發麻。
我們來到一個沙灘,看到漸漸多起來的泳客,修整得平平坦坦的行人路,難得這個沙灘水清沙幼,在皓月高掛的夜空中,海邊的浪一個接一個和岸上的沙接吻,周而復始,美不勝修。倆個人自然的相擁在一塊兒,感受着這夜幕沉沉的美景,心中的舒暢難以形容。
3
這天晚上我和雲哥相約在「巨龍酒吧」見面。
「巨龍酒吧」位於鬧市的中心,洋人很多,酒吧內燈光暗沉沉的,放的是Oasis,Green Days一類型的歌曲,頗有氣氛。
我們倆是在大學的一個酒會上認識的,初見面時感到他人品不錯,舉止也得體,看上去很有善。
雲哥身型肥胖,他自己則堅稱自己是身材健碩;相貌不是特別出眾,有點兒喜感,我認識他時他正在攻讀碩士,不過是一個頗無趣的一機電工程碩士學位罷了。父母是大律師,家境本身是相當的富裕,不過雲哥自己是科技的達人,在外國留學多年,一口偽洋鬼子的口音,回來沒有特別的去找工作,就到大學去讀個碩士學位。
雲哥一手舉起酒杯,和我乾了一杯,滿臉認真的說:「本,你就好啦!我最近真的心情很低落。」
我說:「雲哥,怎麼回事呢?」
雲哥說:「秀那傢伙最近又辦了個聯誼會,說是會請些漂亮女孩來,怎知道漂亮的一個都沒有呢!」
我說:「怎麼會呢?」
雲哥說:「真的喲,你知道我的條件很不錯呀!對女孩來說是有一定的吸引力的,可是為甚麼總找不到相好的女孩呢?」
我說:「對啊,為甚麼呢?」
「我也不知道啊?」雲哥說着嘆了口氣。「就連秀那樣混帳的傢伙也有女朋友啊!」
我說:「這麼說來,雲哥你在找甚麼樣的女孩當女朋友呢?」
「你有好的介紹給我嗎?」他猛地睜大了眼。
我說:「沒有啊?只是好奇問問而已。」
雲哥說:「噢,其實也沒有甚麼特別要求啊,只希望是樣子漂亮、身材好、學歷不要太差就好。」
我說:「這樣的女孩我不認識呢。」
「要是脾氣好就更好了,」他自言自語的說:「是處女也很不錯啊!」
我說:「你不要要求太高就好了。」
我們經常提起的秀是我大學時的朋友,也認識雲哥,三個人相處得很不錯的,因此在畢業後也間中約出來喝喝酒。雲哥在大學常和女孩搭訕,也曾拿過不少女孩的聯絡電話。秀說如果自己是女孩肯定會怕了他,不過怎說雲哥也曾成功過,然而到底是怎樣辦到的仍是一個謎團,因為我從沒有親眼見過。
雲哥說:「不過啊,秀辦的聯誼會上是有一個挺漂亮的女孩。」
「長甚樣子的?不發展看看?」我好奇的問道。
「哈,你以為我雲哥是誰?」接着他取出智能手機,自豪的笑着說:「現在這個資訊發達的世代,沒有最貴的智能手機可是認識不了女孩啊。」然後在自己的相片簿中展示了那個女孩的幾幅相片。那個女孩樣貌相當不錯,看上去感覺很純品,很乖巧的樣子。
我附和著說:「很好啊。」
雲哥說:「唉,不過現在只能叫做前度了。她在聯誼會上已經很留意我,我們談了很多呢!學業啦、大學生活啦、工作啦,可以說是無所不談。」他苦笑着呷了一口酒。
雲哥說:「我們互相傳了很多短訊,有關自己的內心世界,深層次的情感交流。」
說起互傳短訊,我的手機忽然震了一下,是艾娜的短訊。
艾娜:「在哪?」
我:「在和朋友喝悶酒。」
艾娜:「琴我又彈了一下,是很認真的彈啊。」
我:「我想聽。」
艾娜:「下次彈給你聽。」
我:「好。」
「喂,有在聽我說嗎?」雲哥蹙了眉頭一下說。
我說:「有啊。」
雲哥說:「女朋友嗎?」
我說:「不是啊。」
然後我接著雲哥的話,說:「談內心世界很好啊,為甚麼到最後不成功呢?」
雲哥說:「我知道她很喜歡我,我也很喜歡她。雖然沒有說出口,不過我們已經像是男女朋友一樣,還約會了幾次呢。」
「嗯。」我等着他繼續說下去。
雲哥說:「我幾天前約了她到一間高級餐廳,想將我們的曖昧關係弄個清楚明白。」
我插嘴說:「其實就是告白吧?」
「可是!」雲哥突然將酒杯夯的撞在桌上,噹噹噹的幾聲,酒潑了出來少許,我的酒杯也差點兒被他弄跌,他的舉動嚇了我一跳。
「竟然有個不務正業的混蛋搶先一步了!」他似乎真的很氣。
我說:「然後呢?和他在一起了?」
雲哥說:「對啊。我知道她很喜歡我的,可是有甚麼辦法?」
我默默喝了杯酒,洒的味道其實有點酸酸苦苦,不過人們就是因為這樣才喝酒的。
雲哥說:「現在我看到她的照片都會感到很傷心呢!」
「好了,乾一杯吧?」然後我們又喝了幾杯。
由於進入沒有甚麼好談的沉默,我忽然留意到了掛在牆上的電視機正在播美國職業棒球,有New York Yankees,可是讓我留神的是在電視機畫面最下面的一則文字新聞報道。
「……小提琴家演奏會門票銷情不理想,演奏會將無限期延期……」
我說:「你看到嗎?就算是多有名的音樂人,也有不景氣的時候嘛,所以雲哥你就不要消沉下去了,女孩甚麼的總有一天會找到的。」
「我管他甚麼小提琴家,我還是很想她!」可能是酒喝多了,雲哥的說話開始模糊不清。
「現在的人都不聽古典了嗎?」我自言自語。
雲哥則繼續自己的消沉,說:「本,你就好啦!」
另一日夜晚我和秀約了出來,也是在「巨龍酒吧」,剛巧也是在同一個坐位。
秀是在大學時一個很要好的朋友,雖然沒有特別的愛好運動,不過身型頗為健碩,打扮時髦,髮型也是最流行的。秀差不多是我認識的人當中最帥的一個,瓜子臉型,眼睛很有神,一派自信。他也喜歡音樂,不過主要是流行音樂,因為我也知道一些流行音樂,所以也算談得來,而且這傢夥看很多很多的書,博學多才。
酒吧內放的仍然是Oasis的音樂。
秀說:「本,你和雲哥見過了嗎?」
我說:「見過了,說了一大堆他在聯誼會上認識了女孩的事。」
秀說:「對啊,是我辦的聯誼會。」
他的性格很適合做活動的搞手,個人魅力又足夠。在認識了雲哥之後已經辦了兩三次這種聯誼會,邀請了好些朋友去,當中有不少質素不錯的女孩。我認為秀是真心的希望雲哥找到女朋友的。
我說:「怎麼了嗎?你先前的短訊說有甚麼好笑的。」
「又好笑又憤怒就是了。」秀頓了一下,說:「你知道我花了多少時間心力去邀請人來啊,然後在聯誼會結束後他竟滿認真的對我說:『秀啊,這種聯誼會你就別再辦了,女孩根本沒有看得上眼的嘛。而且怪尷尬的,跟沒興趣的女孩也談不上話啊。』」
我說:「不會吧?他不是約會了一個女孩嗎?」
「就是啊!不過那是我後來才知道的。」秀呷了一口酒,說:「他不是在聯誼會上認識了女孩嗎?那女孩是我和女朋友一個挺要好的朋友,後來她跟我們說雲哥約了她好幾次啊!他也不多謝我一下。」
我說:「嗯,那很過份啊!可是那有甚麼好笑的?」
秀說:「好笑的可多着呢!他不是拿了女孩聯絡電話嗎?那女孩說雲哥在短訊對她煩個不停,禮貌上應對了就好,本來就算是約她也不會出來約會。只不過後來雲哥很快就提起自已怎樣的有學歷又有錢,父母是大律師。那女孩其實是很貪錢的,就抱着玩一下的心態去結識吧?有傻瓜宅男出錢請一兩餐高級晚餐也沒有甚麼損失啊。」說完了就哈哈的笑起來。
我說:「雲哥說那女孩喜歡他啊?又談心事甚麼的。」
「他跟你這樣說?」他忍不住笑,差點兒酒也嗆到。
我說:「對啊!他又給我看她的照片。」
說到這會兒,秀再也忍俊不禁,哈哈大來起來。可能因為喝了點酒的關係。
秀說:「他對自己大學學系的同學也這樣說呢!不過,你知道嗎?他是多麼的變態,在臉書加了那女孩好友,然後下載了她幾十張相在手機跟人說那是他女朋友呢!」
我說:「怎麼可能?那真的很變態呢!」
秀說:「有一次我乘他走開後,見他的電話放在桌上,本想鎖了他的電話開個玩笑,好奇之下看看他的相簿,發現他有幾十張那女孩的相片,不過連一張合照也沒有。我也有在臉書上加那女孩做好友,一看就知道是她自已上傳的相片。」
「真的很變態。」我說,不過也覺得很好笑。
說到這裡,我大概知道了故事的始未。
我的手機忽然震了一下。
艾娜:「在幹甚麼?」
我:「喝酒。」
艾娜:「又喝?對身子不好。」
我:「身子本來就不大好啊。」
「那麼,」我抬頭說:「那女孩知道這件事嗎?」
秀說:「不知道,只是我和女朋友商量後叫她不要再和雲哥見面了,反正他們的感情應該沒有甚麼好結果的。」
我說:「然後她馬上就和別的男孩一起了嗎?」
秀說:「對啊。」
我說:「嗯。」
「雲哥還以為那女孩喜歡他。」秀又笑了一陣子,乾了一杯酒,然後倒滿了一杯,又給我倒了一杯,酒精上來,臉紅紅的說:「本來也不應這樣笑他,可是現在的雲哥已經完全是一個變態了,你也別和他太牽上關係,說不定那一天他喜歡上男人。」
「不會啦。」我有點兒反胃,也許真的喝多了。
「乾杯!乾杯!」我們像是慶生的傻瓜,高舉酒杯乾了。
艾娜又發來了短訊:「身子不好要看醫生。」
我在鍵盤上很快的打下:「就看妳嘛。」
艾娜:「哈哈好呀。」
我:「現在在忙嗎?」
艾娜:「不用當值,現在很閑。在家照顧哈哈和包包。」
我:「我可以來聽妳彈琴?」
艾娜:「隨時歡迎。」
我:「喝太多了,我不想吐在妳家。」
艾娜:「哈哈,那麼下次見罷。」
然後我回覆:「好。」
「喂,」秀說:「別只給女孩發短訊啊。」說罷不耐順地又喝了一杯酒。
我說:「是上門調音時的客人啊。」
秀說:「對啊。你好像在做上門調音呢,怎麼了,琴壞掉了?」
我說:「也不是。」
秀說:「是漂亮的女孩?」
我說:「是啊。」
秀說:「你有她的照片?」
我說:「沒有啊,你把我當成是雲哥?」說起雲哥兩個人就忍不住又大笑起來。
秀說:「對了,你怎麼會在做這種工作呢?坐辦公室坐得膩了嗎?」
「對,在辦公室不就像是機器嗎?」可能是酒意上來,忽然想多談談心事的,平時也很少和秀談這些。「有聽說過世界的問題是甚麼嗎?說是『人本來是要珍惜的,而物質本來是要使用的……』」
秀說:「不過現在是『物質被愛惜,而人類被使用』吧?當然聽說過。」
我說:「嗯,說真的啊,從我進大學至走進辦公室,一直都是死掉了的啊。」
秀說:「說得真誇張,那為甚麼不選別的。」
「我認為我是在慢慢的自己殺掉自己。」我接着喝了一口。
秀說:「我以為你會說甚麼『沒有選擇啊,為生活嘛』那種話。」
我說:「我不會這樣說,因為是自己的選擇嘛。除了被世界拋入之後,就是除了出生條件以外,人有意識之後的選擇都是自己要負上責任的啊。如果秀你相信自由意志的話。」
秀說:「沒有自由意志的話,我還不如死掉。《浮士德》好像有內容是關於『人要死的話,神不能迫他活下去』。」
我說:「現實世界是完美的,它就是完美本身,因為它是唯一的世界啊,根本沒有比較的對象,怎麼能不是完美呢?」
「你知道自己在說甚麼嗎?」秀看着我笑了。
「我們也是它的一部份,我們也是美好的,縱然有多麼的不足和缺憾,不過正正是這些不足和缺憾形成了現實世界。」我差點兒要嘔吐。
「我想你累了又喝醉了。」
這時手機震了,連續震了好幾次,我拿起手機一看,是一個很漂亮的女孩打來,原來是敏。
我說:「喂,敏。」我的聽音沙啞難聽。
敏温柔的聲音從聽筒的一邊傳來:「喂,肥本你在哪?」
我說:「還在外面,秀也在。」我提起精神說。
敏說:「你飲酒嗎?」
我說:「對啊,只是飲一點點。」
敏說:「有其他女孩子
我說:「沒有啊。」
敏「哼」的一聲,說:「對了,最近公司的經理老是給我發短訊,明明己經收工了,又發私人短訊過來,真是煩人。」
我說:「他是妳上司,不回覆的話不是會太沒禮貌了嗎?」
敏說:「對啊,那麼我盡量簡單地回覆他吧。對了,你也快點回家吧,很晚了,不要喝太多。」
我說:「好的。」
然後又多說了幾句甜蜜話,回為她要早起上班,所以掛掉後就睡了。
我說:「晚安,敏。」
敏說:「晚安,肥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