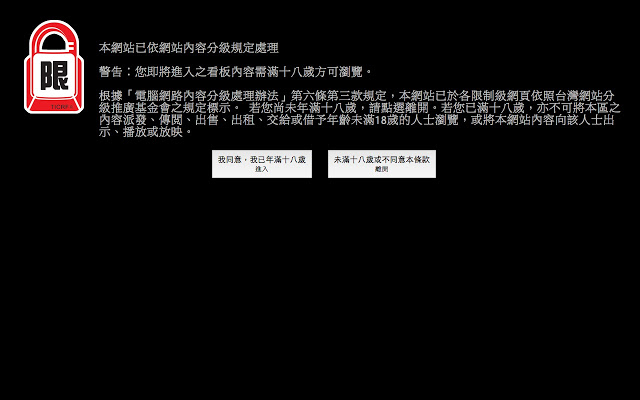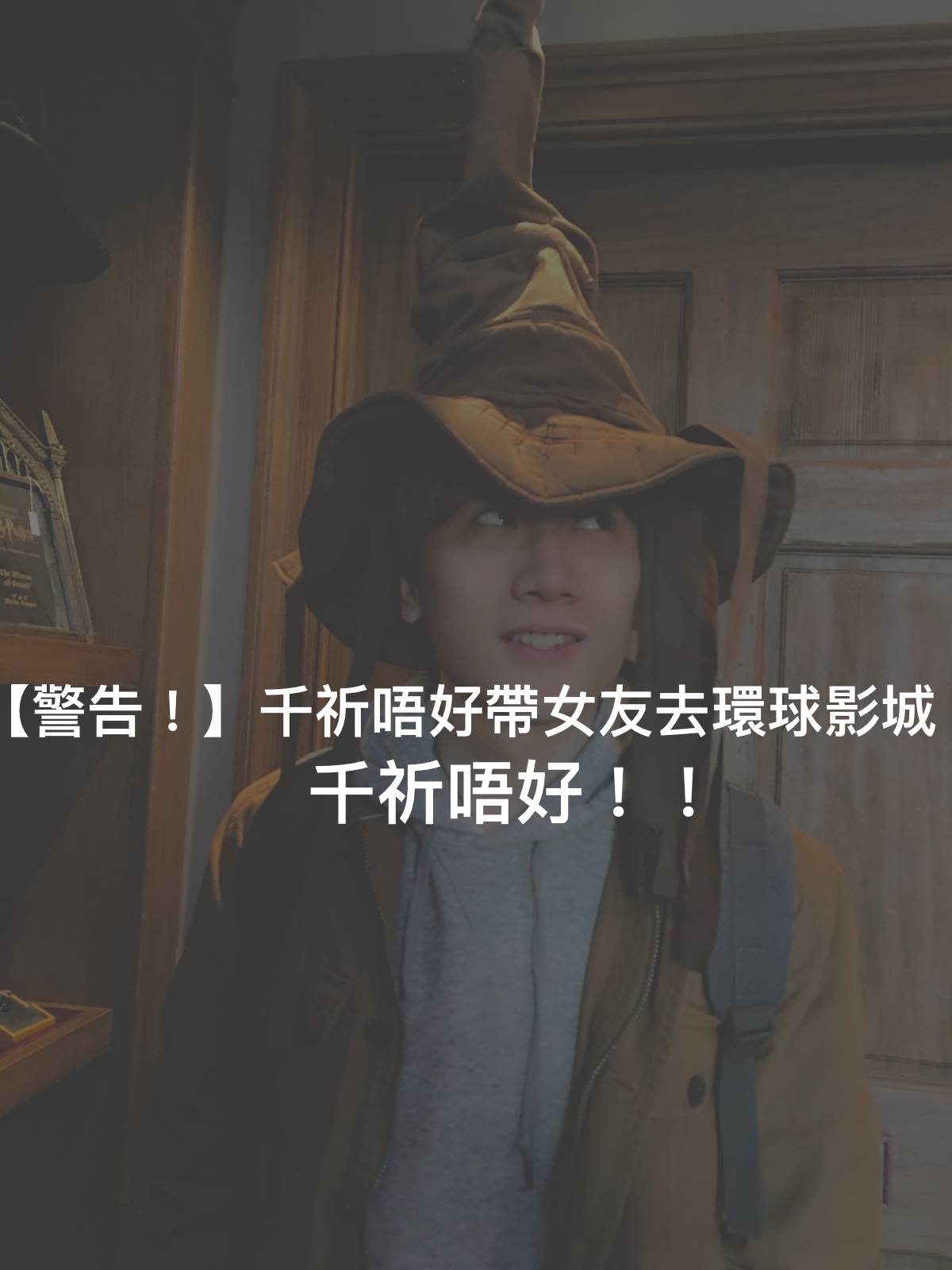他想起,終於獲義工通知可以接小貓回家的情境。
他記得,那時開始被身邊朋友稱為「貓奴」的興奮。
由起初為了更親近愛貓前女友而投其所好,到後來的甘願為奴——盡一切貓奴義務,事先在網絡左搜右尋、詢問朋友;又四處張羅,到十二元店選購自製窗網的材料,耗了一個週末把象徵自由的窗戶裝上圍網。還記得中學時跟朋友組成樂隊,剛好在1989那年6月成立,那時他們帶淚寫下了第一首原創歌曲:《窗口》。
裝好窗網,又被老媽碎碎念。作為老媽這種生物,她總把時機拿捏得異常準確。就在他裝好全屋第九個兼最後一個窗網之時,她就開始念兒子怎麼不待她徹底抹乾淨窗花和玻璃才動手,到底要她以後抹窗多做幾倍工夫云云。老媽年事已高,他不敢忤逆,遂把九個窗網拆掉,等老媽抹好窗再重新裝上。疲倦不堪,卻又不敢鬆懈,生怕有日小貓會因為哪塊窗網繫得不夠緊而釀成意外。窗網有九塊,貓命可非真的有九條。
貓義工前來家訪那天,他還給老媽奉上「額外家用」,支開她著她外出找朋友玩樂,免得她在義工面前亂說話害他前工盡廢。
家訪後義工非常滿意,他順理成章成了貓奴。
為小貓起名窗花,他對窗花的愛日積月累;對女友的愛卻力有不逮,最後分了。但他依然還是窗花的忠心貓奴。
其實他覺得可笑,「奴」字明明帶有貶意。隨著人類文明進步,多次革命與解放,應該沒有人會願意充當或自稱奴隸才對。卻怎麼在這個發達且滿是知識份子的小島,會漸漸出現「貓奴」這個約定俗成的新詞?
在現代社會,被利益誘惑、思想被禁錮的人或會產生出奴性,在香港就有許多受雇人士被壓榨剝削還甘願受苦。那麼貓奴的奴性又是怎樣來的呢?他覺得應該是來自——愛。由喜愛、憐愛到深愛,甘願為一隻小動物獻上心思勞力與時間。自願奉獻的同時又帶點渴望,渴望從中得到被愛、被需要的感覺。在馴養一個目標的時候不知不覺成了專注為他付出的奴隸,也不管對方有否心領。
// 苦困皆自願,心願自信定能圓 //
嘩,多久沒聽過人唱這首老歌。他心想。
人生如朝露,何處無離散。身處這間自租band房,隔音綿內滲透著他廿多年來組過八、九隊樂隊的點滴。然而曲終人散,樓也變空,最後band房就他一個人使用。
他懶得打掃,長年沒收拾,積了一地煙頭垃圾,以及一梳化堆積如山的待洗衣物。最有代表性的要數那個黏滿香口膠漬的譜架。一年夏季他與隊友練習時剛巧冷氣壞掉,只好讓電風扇上陣,卻吹得五線譜如秋季落葉,散落一地。他靈機一觸,把口中香口膠吐出黏住自己的結他譜,固定在譜架,看得眾人目定口呆。
而就在今天,在這個空虛的垃圾場,來了一名訪客——一個男孩,看似二十出頭,他納罕。年輕band界應該蓬勃得很,男孩為什麼要找一個大叔組樂隊?
// 一切皆自願,只管耕耘成敗不去算 //
男孩還懂得唱這麼old school的歌,叫他驚喜。對,男孩不像窗花,男孩是自願前來他身邊的。
一切皆自願,苦困皆自願。
這夜,他自願的收拾起band房來。明明上星期舊隊友上來找他聚舊,說他地方髒,他還狡辯說這叫不羈放縱,說別人懂條鐵。
回到家,餵過窗花,他又走到電腦前在網上左搜右尋,想要知道年輕一輩喜歡的室內風格長什麼樣。什麼?文青風、小清新?他起初苦惱,心想若將band房佈置成這種格調,也太像cafe…… 而且也會把他辛苦經營的「佬味」抹去。但後來想想又覺得這種風格跟男孩的氣質很配。再說band房現在也太昏暗殘舊,確實是時候來些改變。
在搜尋引擎鍵入「band房、裝修、DIY」等關鍵字那刻,他突然愣住。然後又若無其事繼續搜尋。那夜他沒有睡,就一直參考別人談及自行裝修的網誌,以及抄下油尖旺區一些建築材料商店的地址。
其實,他能夠清晰地感受到那些模糊的思緒——但他逃避了自己的內心一整夜,不願去分析自己的動機,不讓自己再三回味那種跟接窗花回家一樣的興奮,不甘被自己以世俗口吻說自己猥瑣。他不願正視自己的情感,不願承認自己的期盼;不願分析「期望把男孩留在身邊」及「自己好像喜歡上男孩」這兩件事究竟是否合理。也不願進一步推想到底在情在理他的感情會否被男孩洞悉、理解、接受。他當起狙擊手,以為自己有能力阻止這些情感由潛意識滲入表意識。
他在每個自己想要逃避的念頭閃過之時,就輕輕哼唱:
// 今天陽光正暖,我的心更暖 //
與窗花對視,一股強烈幸福感湧上心頭,他從未後悔當上貓奴。然後,想著男孩,他又繼續一個勁的計劃翻新band房的事宜。
— 完 —
文: Cheryl Yu
Picture from a book, “Oh, art is too hard.” Andy Warhol
fb: https://www.facebook.com/Chery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