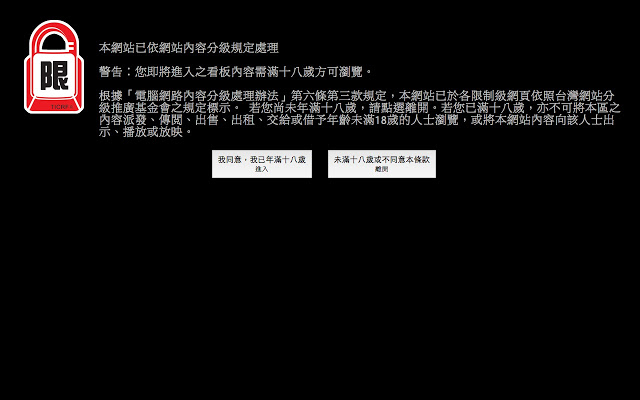我想死。
大概,如果那時候沒有參加這個計劃,我早就死了。我真想時間回轉,雖然現在的我對時間觀念愈來愈淡薄。
「我想死。」
我對面容陌生的年輕男子說道,而這個人應該是我父親。如果當時他和我一同死去的話,享年大概有六十多歲了…… 又或七十歲,我記不清楚。
他微微一笑,咀嚼肌上露出一雙我從未見過的酒窩。我沒有問他為何又改變相貌,在意的反而是那幾句突然被憶起的歌詞 —
// 梨渦雖俏,悲歡竟逆料,樂極痴戀變恨苗…… //
啊,是老媽以前愛邊做家務邊喃喃哼唱的老歌。
「爸,媽不在這邊,她來不了。」
「我知道,所以我和你一樣,我也想死。」
但我們卻無法逃出這個「極樂世界」。
我和爸在一股濃重的煤氣味中被救過來後,從社署人員手中接過文件,簽妥後,做過簡單的身體檢查便來了這裡,沒有威迫,沒有痛楚,一切自願。
還記得計劃名叫《自殺以外的另一選擇》,很顯淺易懂,也算體貼,起碼沒有再讓厭世並一心尋死的人去消化那些矯情又一味鼓吹正能量的無謂資訊。對於那時的我們來說,是很易入口、很順理成章會去接受的方案,畢竟想要離開現實世界的心態從未改變。
爸想離開的,是那個失去老媽的世界。媽曾經高齡懷孕,繼而難產。未曾在世上呼吸過一口氣的弟弟,就因缺氧而窒息失救。老媽的命保住了,卻不再是從前那個老媽;身體漸漸復元,精神卻出了毛病,性情大變。老爸無悔無怨照顧她,不管有沒有忽視家中的另一成員 — 我。他除工作以外盡可能對老媽形影不離,甚至缺席我的大學畢業典禮;不管家中經濟壓力如何,不管我有學債在身,在我出身後堅持提早退休陪伴老媽,家中開銷僅靠我一人收入。
可惜他對老媽多年的體貼仍未能彌補醫療制度上的不足。
媽的病情每況愈下,最後幾年甚至開始出現幻覺及嚴重失眠;而公立醫院精神科每次覆診的輪候時間卻需要一百二十五個星期。
最後一次見老媽時她說她很快就會帶弟弟去荔園看恐龍和游水,我不以為意。當晚她就在我們熟睡時獨自外出;第二天我們接到消息說在海濱公園對出海域發現她的屍體。
失去了媽,我和爸漸漸沒有交流對話,因為以往所有話題都是圍繞著媽。
失去了媽,我開始想死。
我重新檢視自己和這個世界,感覺我好像不再被這個世界需要。家裡再不像從前般需要我。老爸去了當看更,家裡少了個人,又多了份收入。他口裡說是替我減輕負擔,但我知道他其實只是不想再長時間逗留在那個老媽待過的家。
公司不再需要我。在大行任職採購員九年多,還未升過級,就被栽員。即將成為過路人的同事議論紛紛,說早就知道這是夕陽行業,問我有否打算轉行,我一時答不出來。多年來我一直心不在焉,從未審視過工作前境;在我而言,工作的意義從來就只是為家裡帶來收入,好讓我們一家三口有飯吃。
女友不再需要我。最後一次見她時,她哭著控訴說我不愛她。我沒有挽留她,大概是因為我根本說不出「我愛她」。怎樣為之愛?爸對媽的是愛?怎樣為之不愛?像爸對我那樣?她又言之鑿鑿說我還留戀著前度 — 那個我早已忘記相貌,只記得在我媽出事後便一直不敢到我家作客的人。就因為我常常跟她提起舊時……但其實我就真的只惦記著舊時而已,那個老媽還是老媽的時代。
於是女友又成了另一個前度。其實我很喜歡她肌膚與體溫曾經帶過給我的慰藉,因為感覺很真實。我討厭言語,我認為那不過是每人各自在腦海裡的幻想,就像老媽經常自言自語說那些有的沒的。
連學債都還清,跟這世界最後的羈絆都斷了。
我沒有哭,在媽病發不久我就再沒有流過眼淚,但卻不是因為我相信那些「男兒有淚不輕彈」的廢話。其實在媽患病初期我常常忍不住哭泣,而每當被媽看見,她都會上前像哄小孩般安慰我……但口裡叫的卻是從未誕生弟弟的名字。漸漸,我覺得噁心,就沒有再哭過。
失業獨留在家的第一天,我翻看了兒時相片。相片不多,只有薄薄三本相簿,不消十分鐘就看完。
「好像已經無事可做。」
我忽然自言自語。
「天氣很冷。」
我接著說,好像真的會有人聽到一樣,繼而把門窗都緊緊關上。爸平日習慣開著木門讓室內空氣流通。
再走到廚房,開了煤氣,然後把爐具的煤氣喉扯脫掉。
「我想睡一覺。」
我躺在梳化上,心想真有趣,這句大概會成為我的遺言。
突然,開門聲把我嚇到,老爸回家。
他像已經知道我在做什麼,卻不發一言,關上門,然後同樣躺在梳化上。
也好,儘管父子倆在生命路上未能相依偎,至少在最後關頭也同路。
後來就一路同路至這個「極樂世界」……
或許你會問,究竟我們身在何處?我們參加了甚麼計劃?《自殺以外的另一選擇》是指甚麼?
你可以將其想像成新世紀福音戰士裡的《人類補完計劃》 — 將人的意識聚集至同一處,使人心互相補完。參加者自此不再需要肉身,人將永遠活在意識層面裡,不會消逝。由於沒有任何物理限制,參加者從此不會再受現實所束縛。各人甚至可以在新世界裡隨意交流;想像並體驗各種生存方式;無限建立自己的理想國度;隨意改變自己的形態。沒有疾病、死亡、貧窮及傷害,人人自給自足的在意識裡得到永生,從此遠離生死疲勞。
不同的是,在背後策劃的並不是神或外星人。推動《自殺以外的另一選擇》的是中港兩地政府。沒有神力,單純以科學技術成就此計劃;可想而知背後有多少法輪功學員和政治犯因此淪為試驗品。計劃成功推行,反應熱烈,一下子解決了許多民生問題,還被西方國家大讚做法人道,紛紛仿效。從此香港不再有土地問題、貧富懸殊問題、教育制度問題、醫療制度問題、人權問題……因為不再有人提出問題,不再有人因為解決不了問題而自殺。大家都去了「極樂世界」。
而我和爸卻開始想要回去。想回去死。
沒錯這裡是應有盡有,我們從此不再貧乏。但正是因為我們甚麼都能擁有,因此擁有的感覺就變得很虛無。
漸漸,我們又再感到空虛、空洞、寂寞。
而且,雖然可以盡情想像,我們卻無法把現實裡老媽的意識帶來這裡,因為老媽一早已死,就在這個計劃推行之前。
漸漸,我們又察覺到原來在這裡我們無法選擇死亡。
在這裡我們可以選擇許多生存方式,看似比從前多了更多選擇;但原來我們卻無法依自由意志來選擇「死」,我們只能「生」。我們永遠無法安息。原來我們比從前更不自由。
你以為我們沒有嘗試尋找方法回去嗎?
我們有試過的。我們在這認識一個前醫管局公務員,他告訴我們已經沒有方法回去。
他說,所有參加者的身體在參加計劃時,已永久收歸政府所有。
他說,他曾經參觀過計劃所有流程。
他說,他見過參加者全身所有器官被採摘至一項不剩 — 除了腦袋,就連眼角膜也被雙雙割掉。
留著腦袋,除了是因爲需要維持住參加者的意識;更重要是香港人的腦袋在器官市場裡不值錢……賣不到價。
他說,其實在現實世界裡的人都隱若知道計劃背後陰謀;只是,大家看到社會變得和諧,就覺得滿足了,沒有人追究,反正被賣器官的又不是自己。
我們問他,為何明知計劃真相還要參加?不會不甘心嗎?
他說,反正都已經得永生了,WHO FUCKING CARES?
— 完 —
文: Cheryl Yu
Photo: 電影《藍色大門》劇照
fb: https://www.facebook.com/Cherylism/