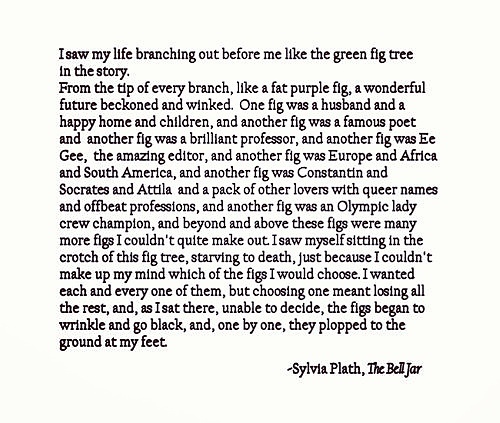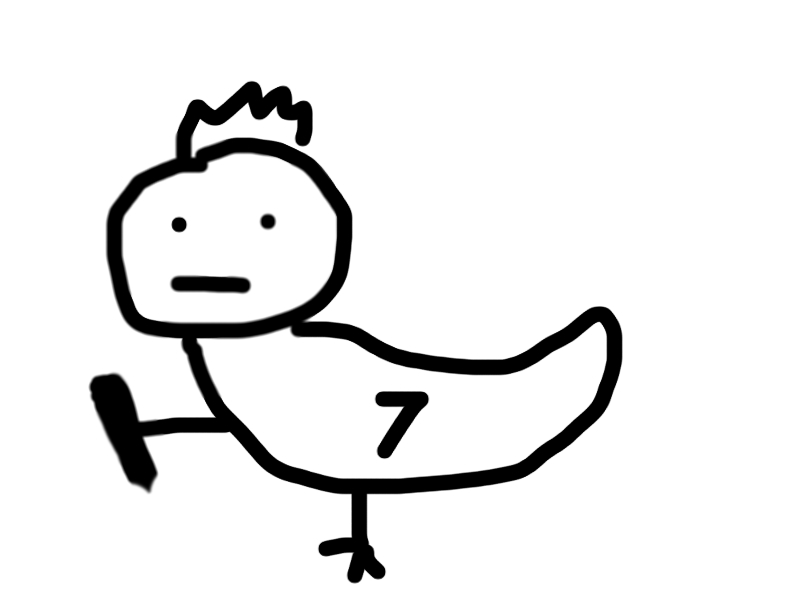IG: @everythingunknown
本文涉及對紅燈區以及內心之真實敏感描寫,敏感病人請自行迴避,莫怪我「發佈內容未經防火牆過濾」。
父親說泰國芭提雅是「無眠城」,我以為是我城「不夜城」的結拜姊妹,
原來「不夜城」終日如白天運作,「無眠城」無眠只因精彩在十點後。
時已十時半,仍在街上流連。
父親說那年我只有三歲,到訪此城卻不適合「夜蒲」,
今年十六,好像長大了一點,要去見識世界。
於是我們同瘦弱的啼叫的流浪貓和無家可歸的或爛醉如泥的流浪漢在此暫留。
水汪汪的貓眼有乞求之意,但牠沒有說甚麼。
鄰街的燈紅酒綠,是另一種乞求。
那裡有殘障的乞丐,為五斗米折腰,或者為五斗米假扮折腿。
那裡有美艷的少女在路的兩旁酒吧門外擺賣,為五斗米折腰,為五斗米被年老的白人帶上酒店房間,為五斗米張開大腿,為五斗米呻吟。
那裡有年老的白人,為使少女折腰而付了五斗米,為帶她上酒店房間魚肉而付了五斗米。
那裡有成群的團友,旗幟寫上某內地旅行社名稱,一群觀光客為看熱鬧,也來付了五斗米給旅行社。
那裡有捂住雙耳的我,來「長大成人,見識世界」,付了比五斗米重的代價。
那裡還有父親,他說這裡是「有女」的好地方。
年老的白人為豬八戒,
琳瑯滿目,自然抵不過原始慾望的挑逗,眼光不由自主搜索獵物……
那頭髮蒼白的阿叔在人群中逮到了兩名嬌小的泰國女郎,
不知是男是女,是人是妖,
他們三人聊了幾句便匆匆牽著手走了,
我亦非唐僧,四處張望,
她們穿上不同制服以不同語言勾搭各國旅客,
穿著暴露的羽冠舞衣以軀體勾勒舞步的弧度,
忽然以近乎赤裸的驅體貼近某個陌生人,摩擦兩下,耳語幾句,便牽手離去。
燕瘦環肥,酥胸蠻腰,秀色可餐。
看到個金髮碧眼的美人,身穿半截恤衫外露惹人遐想的曲線腰肢,
她看似旅客之一,也是我無法理解的,街上似乎女人比男人多,
有一矮小男人擋在她面前,說了句話,我聽不清楚,
那美人便投以鄙視的目光,另找路徑逃走。
有人向我和父親說了句「你好」,那是半個美麗的姑娘——
街上也不知多少美少女僅為一半。
然而此刻發現生理一直沒有如常反應,褲襠並無作好準備,
我開始迴避目光,迴避各酒吧門前的美少女戰士陣營,
一如初上街,尚未料及此情此景之時。
我想的事不在她們性感的軀體或優雅的弧線上,而在背後。
如此燈紅酒綠,紙醉金迷背後,
有多少段背棄與傳承的故事——貧窮是一個跨代問題。
窮人的骨氣彷彿無法生存,人們才理解娼妓,
「笑貧不笑娼」的真正荒唐在此。
思想重回肉體層面,
有一刻覺得那些老人極度噁心,利用他人相對的貧窮換取魚水之歡。
不屑得將近嘔吐之際,
自省,免費利用他人軀體作視覺享受亦為一宗大罪,
如此我豈非同流合污之鼠輩?
瀰漫的罪疚感與酒吧樂隊的deathmetal使我無法安寧,
捂住雙耳,閉合雙眼,又直覺周圍每個人都像扒手。
人多擠迫,而草木皆兵,
有個偷偷走過我身旁的男人,
原來只為捉弄前方好友,
卻幾乎被我喝停,
隨後我每走一步都碰一碰銀包電話。
那是一種奇怪的感覺,大概因為昨日看了電影Focus。
我又回想起巴黎的文雀,那一個擔驚受怕的星期。
那個地方叫Pattaya Walking Street,
噁心的人們有空來帶個女孩走,
也許她會當你大恩人或者大老闆也未定?
原來紅燈區酒吧的燈的確腥紅,
而我的不安說,
我似乎還未準備好接受世界和自己的醜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