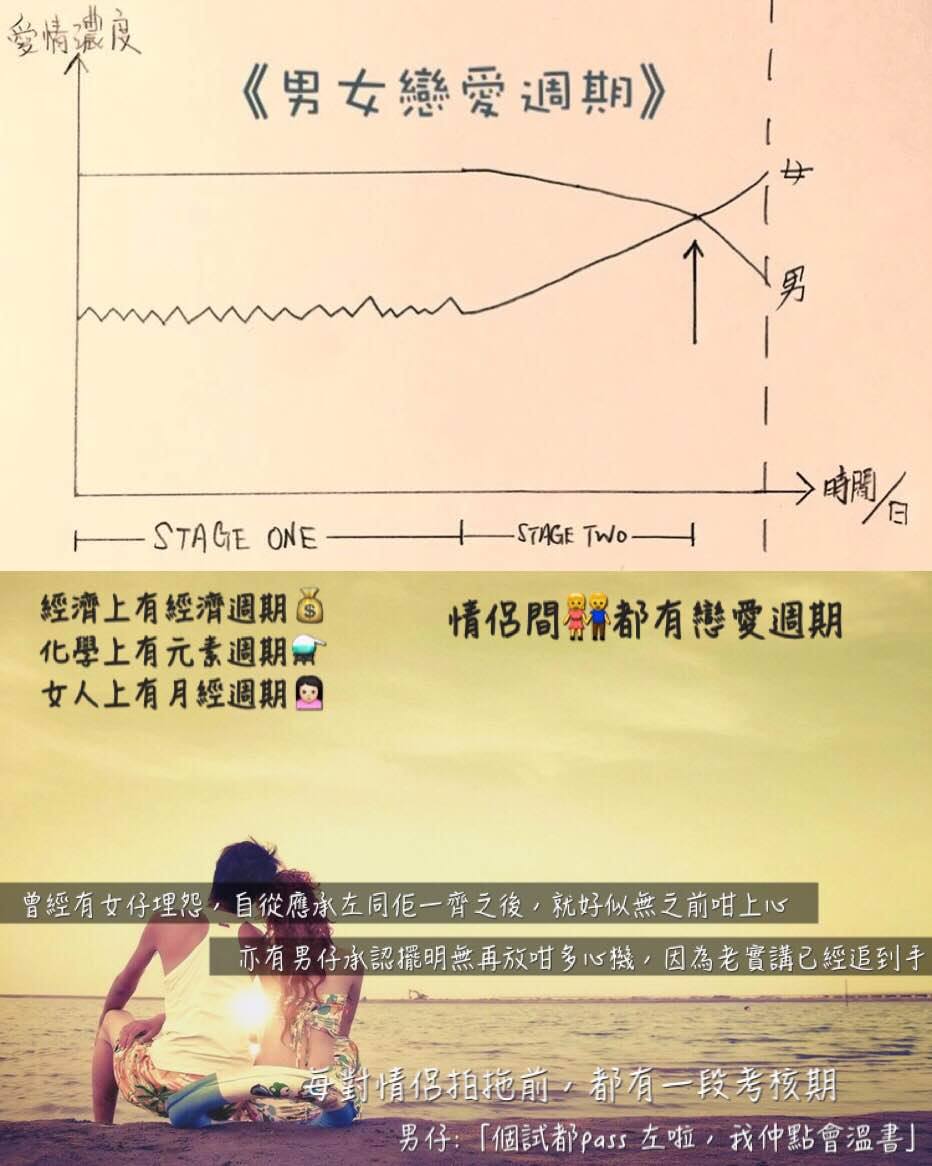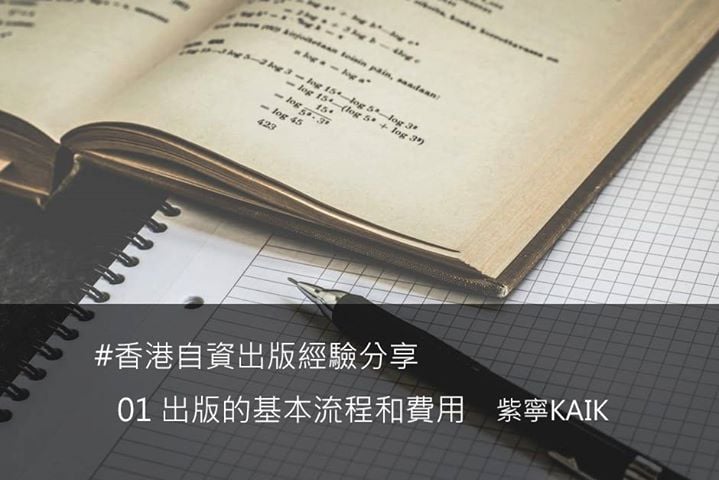「嗚呼哀哉,我欲仁斯仁矣,然天下歸仁,舉步維艱。」講究義命分立的孔夫子,亦不免遭莫之致而至之的命所困惑。禮崩樂壞,回天乏術乎?他仰之於天,夜觀星象,暗道局勢坤上離下,渾沌不明。莫非天喪我?天厭我?
然而風忽爾狂吹,引得孔子扭身一看,竟乃南冥也。一轉三萬里,孔子仍處之泰然,順其自然。此處人煙稀少,卻有一碑一鳥一人。未待看清碑文,躺在鳥上的人道:「汝乃孔老頭子吧?真累累乎若喪家之狗。」輕佻的老頑童續道,「所謂仁心,所謂大同,浮雲而已。子非我,安知我之善?汝若回頭,是岸還在。」
孔子聽罷,默言沉思。正當那老頑童笑容滿面,欲著大鳥一飛沖天之際,孔子揚首挺胸曰:「人禽之別幾希。我之謂人,仁心也,此乃人類之間休戚與共、共情同感之表現,不可廢也!己所不欲,不敢施、己欲逹之,先逹人。吾俯仰無愧無慚。」
「待於一事,有執有失;順乎自然,無為不爭。有曰:有無相生,難易相成,善亦不善。故大道廢,反有仁義。絕聖棄智,民利百倍。絕仁棄義,民復孝慈。」
未待老頑童喘息,夫子即曰:「若夫大道,禮之本為重,世可易禮可改,然仁義不廢,如此則以禮導善,大同世界指日可待!我之謂善,人皆愛之,因發乎情止乎禮。」
「吾不爭於口舌之間,正所謂相反相成,既有我輩無為者,自有汝等有為之士。然於我而言,我之謂人乃道心也,道法自然,不禁其性,不塞其源。」說罷大鳥高飛,須臾不見。夫子瞪著碑文:「相濡以沫,不如相忘于江湖。」不禁喟然慨嘆,君子任重而道遠,豈可置身事外?既然脈絡下的理分如斯,君子只有迎難而上。
一味避世超群,心安乎?嘗未一試,便扼殺可能,當真大道乎?當真道法自然?曇花無悔此生一現,不亦囿於爭奇鬥艷,而忘長生?由是觀之,性者各有差異,既我之性為仁,順其自然,建立理想仁德社會,有何不可?
忽地梵音裊裊,撫順孔子內心之躁動。子略有所明,轉身入廟,卻未見一物,問道:「可有巫?」未幾一僧人無中生有,合十鞠躬:「五蘊皆空,諸行無常,有無又教人怎辨?萬物本無自性,一切皆空。觀汝勞勞碌碌,乃尚未勘破諸法無我之意啊。」
孔子見怪不怪,半响道:「我即仁。眾人皆有向善之心,若能盡其性,則君子也。我輩自有其性,何以一切皆空?」那僧人道:「汝誤以無常當有常,又何苦?諸法無我,現世各事,乃因緣和合而生,此有故彼有,此生故彼生,牽一髮而動全身。故我等固無自性,亦無力控制世事。」
孔子忽爾思憶往事,心有不甘道:「世界固是流動莫測,然人定勝天。一人之力弱,萬人則愈強,萬萬則其勢不可當!君子知其不可為而為之,義命分立。」僧人嘆息道:「意欲無止境。小康,或是大同,汝亦會未會滿足,只有明瞭一切皆空、一切皆苦,才能躍入湼槃靜寂之境,爾後才能滅除痛苦。」
他無悲無喜的續道:「可惜你我緣份至此,不能窮究其中。請進此門,隨緣而行。」孔子依言前行,但不忘回應道:「我輩講求取之有道,凡事喻於義。若能義以為質,中庸行之,何懼欲求不滿?」
「又,汝以為萬物皆空,需互相依賴,此言善哉。然人而無仁,如何相互相生?天道無德,萬物豈能生?德者,重中之重。你我確是道不同,不相為謀。」
孔子隱隱興奮,大道愈辯愈明。待其踏出走廊,重見天日之際,赫然驚覺景色迥異。驀地一男子竟從墳墓破土而山,與夫子雙目對望,片刻說著異邦話來,奇怪的是孔子對應如流。「久候東方智者,願神之國顯現於寰宇,無分你我。汝恭順溫和,懷救世之心,難能可貴。然人皆有原罪,個人之力無以償還,惟信奉天主才能得求,才能賜予永生。」
「子不語鬼力亂神,吾鞠躬盡瘁數十載,亦力有不逮,未能事人,又焉能事鬼?況且為仁由己,而由天主乎哉?我行仁義,非喻於利,非喻於名,非喻於永生,只因此乃人之尊嚴所在!君子內省不疚,夫何憂何懼?」
那人笑道:「爾行善之心,確折服我也,吾亦不願汝永生受苦。望你平心靜氣,上通於天,感悟天主所在,進而察覺人之渺小,不再逆天而行。」「天主要有光,便有光,無所不能。只恨原祖貪婪,我等後裔無不處於待罪之身,更與天主失去交流。」
「巧言令色,鮮矣仁。汝有證據乎?」
那人卻道:「汝謂仁,又可證?」孔子聞之氣極反笑,思索片刻道:「乍見有子溺水,人皆欲救。非為名為利,義之當為也,仁心也。」那人卻是不欲多辯,邊走邊道:「未能彰顯我主之名,則有所偏失,未至完美。願主之榮光早日光耀東方。」
不待孔子回應,一股酒香飄然而至。「東方智者,吾乃柏拉圖,來舉酒暢飲吧。」夫子扭身觀察,卻見一人放浪形骸,躺臥在地,於禮不合,惹得孔子眉頭一皺。待孔子回眸,那人早已無蹤。
柏拉圖視若無置曰:「汝毋庸理會那胡說八道的小子,若吾師還在,定必嘲笑所謂的神,那不過鏡花水月,子虛烏有。」諷刺的語氣卻帶著悲嘆。半响才道:「渾渾噩噩,生之無趣。然好勇鬥狠,求建功立業者,不過自私耳耳。吾以為有愛者,才不枉此生。愛者,至極善之塗也。」
孔子對之曰:「善哉!仁者,泛愛眾。若能愛澤萬民,可謂君子也。」柏拉圖聞之曰:「非也。愛之終點出凡脫俗,凌駕一切善美。汝所謂之仁不過其中一物,非我所欲。」「美之極,即美也,不屬萬物,超越所有。人能知之欲之,緣塗追求,可謂美滿人生。」
卻是此刻風起雲湧,異象突起,景色猛然倒退,彈指之間重回魯城。然孔子再無困惑,亦覺柏拉圖之說法毋庸回答,蓋因:「君子和而不同。我之所欲,人或不欲。可是若天下歸仁,則人無私慾,則人欲逹人,如此所有想法俱能並存,豈不是至善至德嗎?為了眾人,舉步維艱又何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