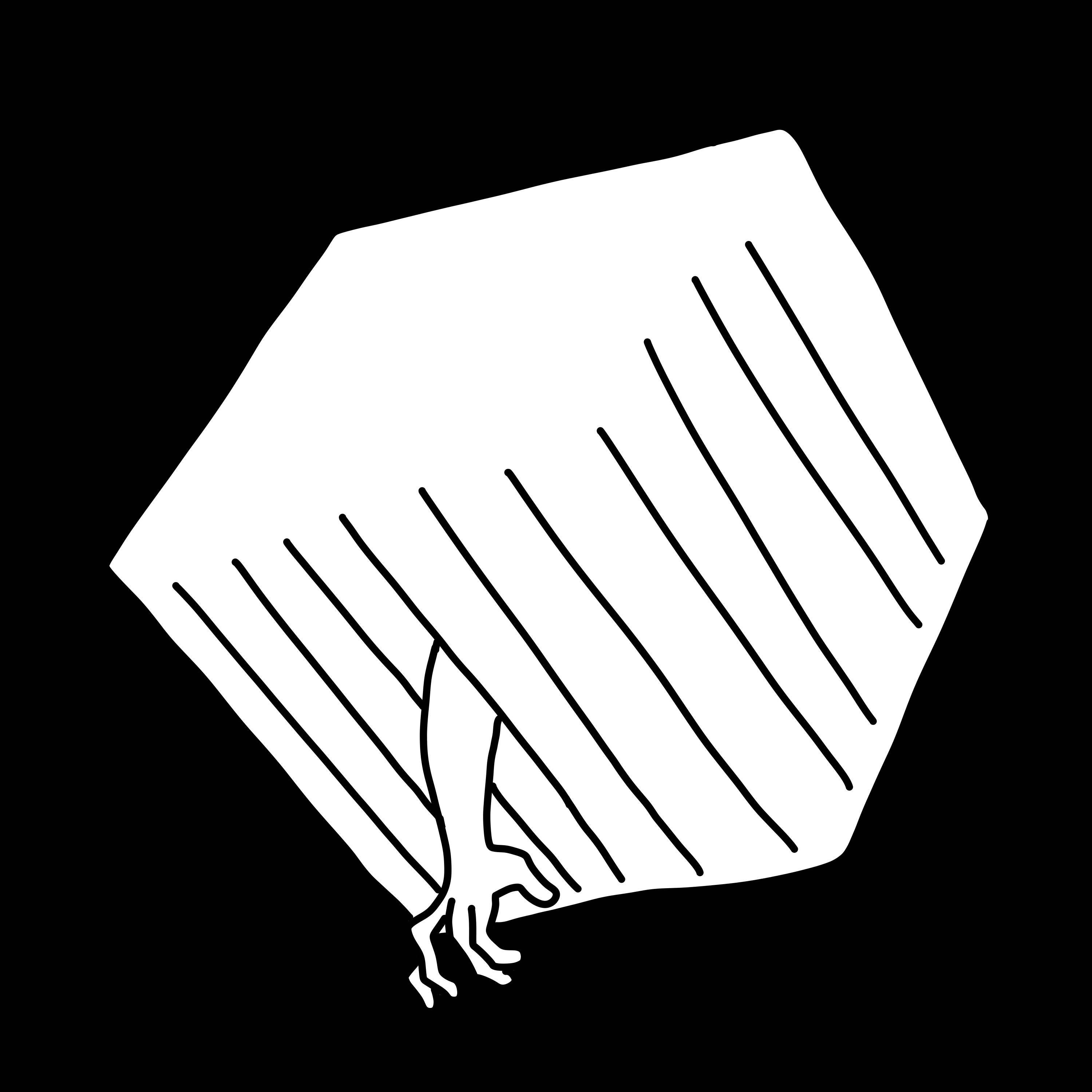「許?阿姨喎。」王志庚說。
我放眼看過去,眼見是一位老婆婆,依舊是那滄桑的臉孔,依舊是那鏽舊的單車,上面挷著一箱二箱,掛著大小二包,蹣跚地在馬路上穿插著,和馬路上隻隻鋼鐵猛獸相比,她顯得更有渺小,但卻發出無比耀眼的光芒,那叫做生命力吧。
阿姨阿姨......從來我們都叫佢做阿姨,沒有人知道佢的名字,只知道每一次在你需要她的時候,她就會出現。
我第一次看見她,是在小學的露天操場。我小學有個挺有趣的機制,往往放學後,露天操場就開放公眾,往往就來了一群又一群的中學生來打籃球,同時也招來了阿姨。
那一天,我踏出校門,天色已晚,看一下手上那電子膠錶,已是晚上七時多了。身為一個小學生,理應及早歸家吃飯去,但因老師罰留堂令我心有不快,卻勾起我叛逆的心,決意流連一會兒。
眼尾瞄到一個熟悉的身影,正是同校的姐姐,是親姐姐,不是嬉戲玩笑的那種。她這個優等生,應該是老師舉辦甚麼活動之類的小幹事吧,所以才這麼晚放學。
「家姐你起度做咩?」我上前問她。
「啱啱幫完老師手。」果然不出我所料。
「食少少嘢,我肚餓。」她說。
「喔...」我答。
她引領我到學校的露天操場,籃球場有著形形色色的人,有的是高年級生,有的是鄰近中學生,有的是光了身子的金髮哥哥。我倆繞過去,走到平時放學後才開的大鐵閘。
有個老婦人,倚著單車。淡黃的街燈照出她一身頗黑的膚色,臉上已有不少代表年歲的符號。她的眼都瞇了起來,成一道線般,看起來就是一臉的憔悴,一臉的滄桑。
「阿姨!」家姐率先走過去叫喊道。
阿姨見狀,嘴角上揚了一下,透露了她的歡欣,問:「要咩呀?」
「雞脾。」姐姐爽快的答,伸手放下了一早準備好的幾個大元,放在那粗糙的手心。接下來,阿姨打開了一個箱,傳來一陣肉的香氣,從中取出了一隻肥大的雞腿,遞給姐姐。
姐姐毫不留情一口咬下去,嫩滑的雞肉在空氣中曝露了,洩漏出淡淡的白煙,那是美味的證明。
我看愣了,姐姐見狀,一盡了姐姐的本色:「我請你食一串啦。」我聽得歡欣,不禁叫了聲好。
我要了一串三片的紅腸,才只不過三元,再加上自製樽子所裝的沙嗲醬,老實說,賣相真的是略為遜色,但一咬一下去,紅腸外邊正正烤個香脆,配上沙嗲醬更是妙絕,令我驚奇的是,在那破舊發泡膠箱取出這一串的紅腸,竟然還帶著烤完不久的温度,實在令我讚嘆。
自此一嚐,偶爾的罰留堂,都有著那麼樣的先苦後甜,每一次留堂過後,我都拿出那時辛苦儲起的幾個大元,一次又一次,買了一串又一串的紅腸。
後來不記得甚麼原因,可能是我變乖了交齊功課,還是小學訓導主任的勸喻,就有那麼一段時間沒有光臨阿姨。
「你第一次見阿姨係幾時嘅事?」我問王志庚。
「中學囉,好似係。」他答我。
「咁遲嘅,我小學已經幫襯開。」我說。
「玩家嚟喎你......熟客仔......」他暗道。
男孩子在青春的時候,總會迷上一兩項球類運動,像是總要揮灑一下汗水,像是會變得師兄長們的帥氣,像是會運動就可以引來一兩個女孩子的青睞。在球場一個二個胡喊亂叫,有時夾雜著髒話,宣洩自己對分隊的不公,宣洩對對方過分行為的不滿,或者純粹的無聊。儘管過程是怎樣子的不快,揮灑汗水過後,每一位也是會打成一片,坐在觀眾席聊個天昏地暗,然後別過,明天再捱過一輪填鴨式的教育後,就再一次到球場揮灑汗水,那是男孩們青春的浪漫。
在這青春的寫照少不了阿姨,每個少年在球場上全神貫注追住球跑來跑去的時候,總有一兩位比較平庸的成員在球場上分神,往往這些傢伙,即是我,就會發現阿姨的身影扶住單車,緩緩走進來。此時就要一聲大叫:「阿姨!」一聲號令下,球場上的皮球不再吸引,大家的視線都轉移上阿姨身上,大家就自由得出一個共識的小休,然後一窩蜂圍上阿姨,要東要西的。
阿姨在這些日子裡,也進步了不少,那頹斑斑的單車,比以前多了一個發泡膠箱,又多了幾條攀山繩固定住一個個大箱小箱。打開新的箱子一看,裡面舖滿冰,輕輕撥開那層冰,一支支汽水曝露了出來。對於那時候的我們,一身臭汗又渴又累,看見汽水上的水珠,猶如寶石般閃爍。馬上抽起一支,遞了二十大元紙幣給阿姨,等不來阿姨的找續,先打開,發出那清跪的響聲,馬上大喝一口。
可樂一下了充斥口腔,在內打滾發泡,再加上那極致地令人愉悅的甜味。我這個口渴又貪婪的孩子,持續地喝下一口又一口的可樂,一下一下衝擊我的喉嚨,那種及時的解渴,是無比的舒暢,那一刻的美味,是不可被取替。
「下?咁嘅?」有個同學驚叫,我向那邊看了過去,他握住支可樂,但裡面卻有著發白的東西。我走近仔細看,原來是由可樂結成的冰。一經了解,原來是阿姨自家製的凝冰可樂。那時凝冰可樂尚未普及,同學們都看得眼睛發亮,像是看魔術表演一樣,而阿姨的樣子,也顯得得意洋洋起來。
那些愉快的日子,永遠都不能長久。學校那邊,功課開始多了,學業開始忙了,就算自己有空,別人放學也只顧忙那些麻煩的功課。漸漸地,再去球場也不再是滿場的同學,而是一個個mk金毛,一個個瘦骨仙赤裸自己的上身。後來,學校更勸喻我們,不要光臨無牌小販。。我那段關於運動的青春,就這樣結束了。我也自此再沒有見過阿姨了。校內不久也有傳過阿姨的消息,有人說她病了,有人說她賺夠收山了,更有人說她的子女很幹,養起她,她不用再這麼艱苦地工作。
而真相呢?我想真相就是我眼前的事實,阿姨變得更滄老了,繼續在這塵世為兩口飯打滾著。我看她蹣跚地推著著那充滿銹斑的單車,一步一步在馬路上走著,繼續在這殘酷的世界生存,繼續散發著那股頑強的生命力。




.jp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