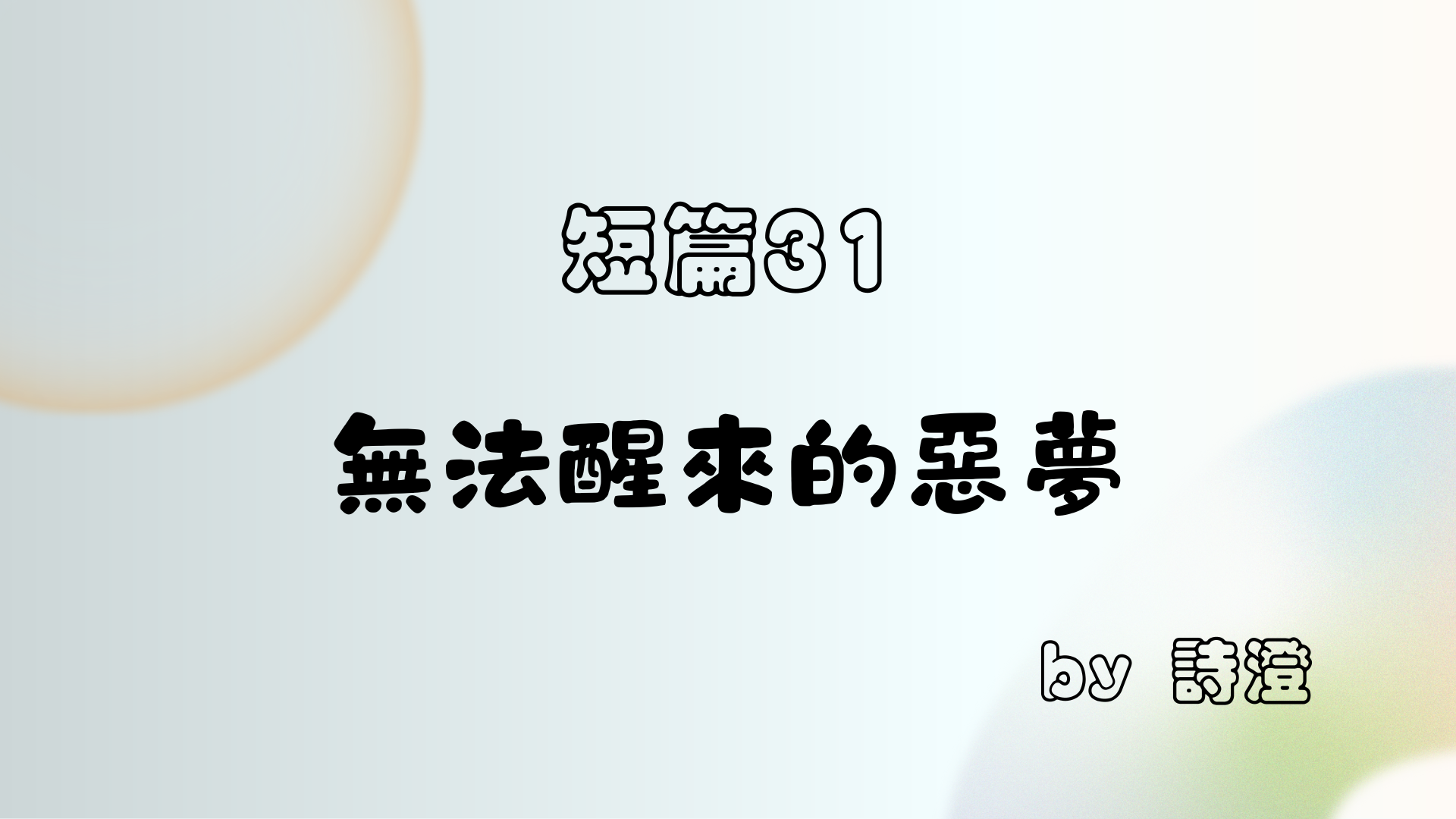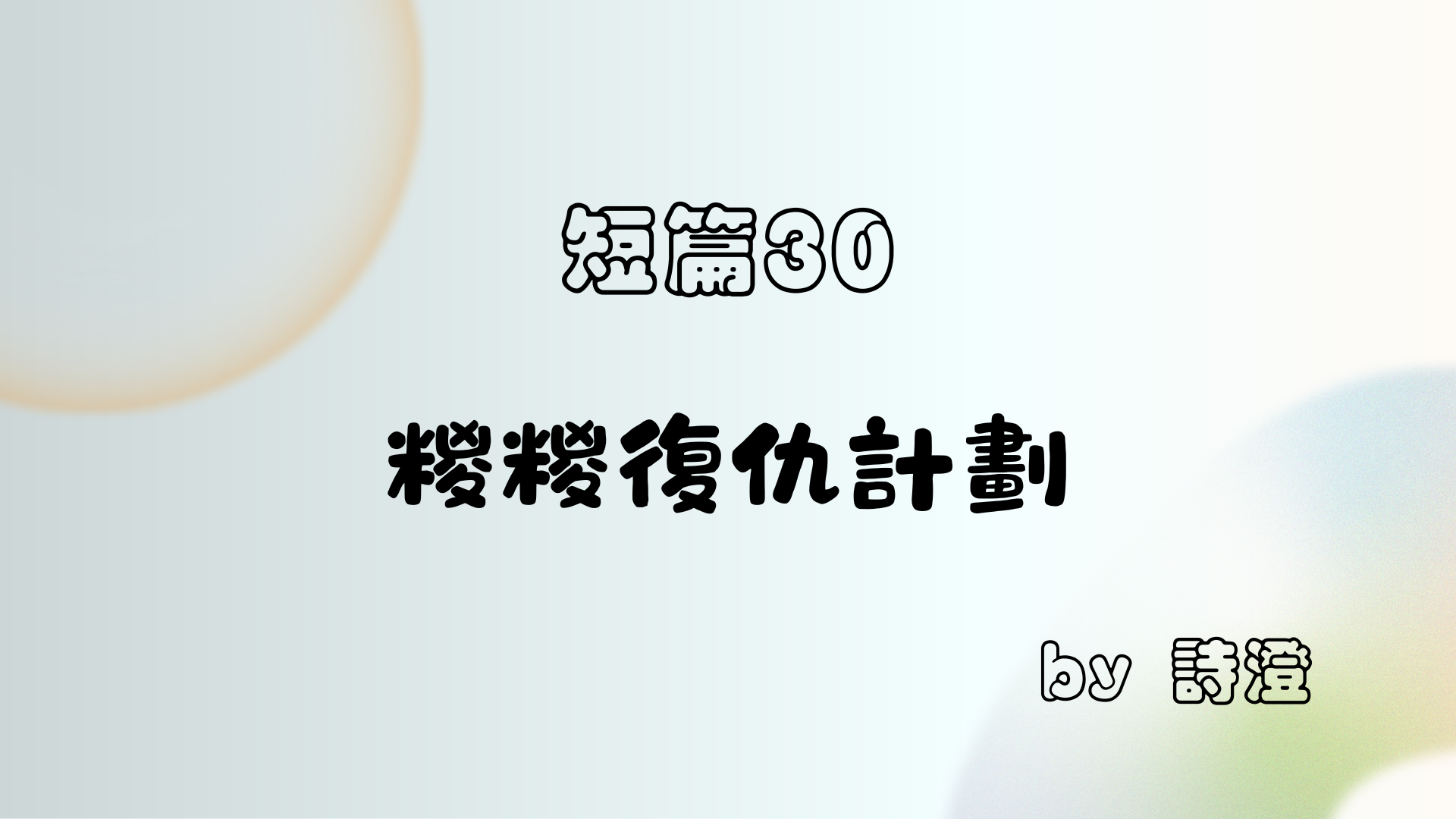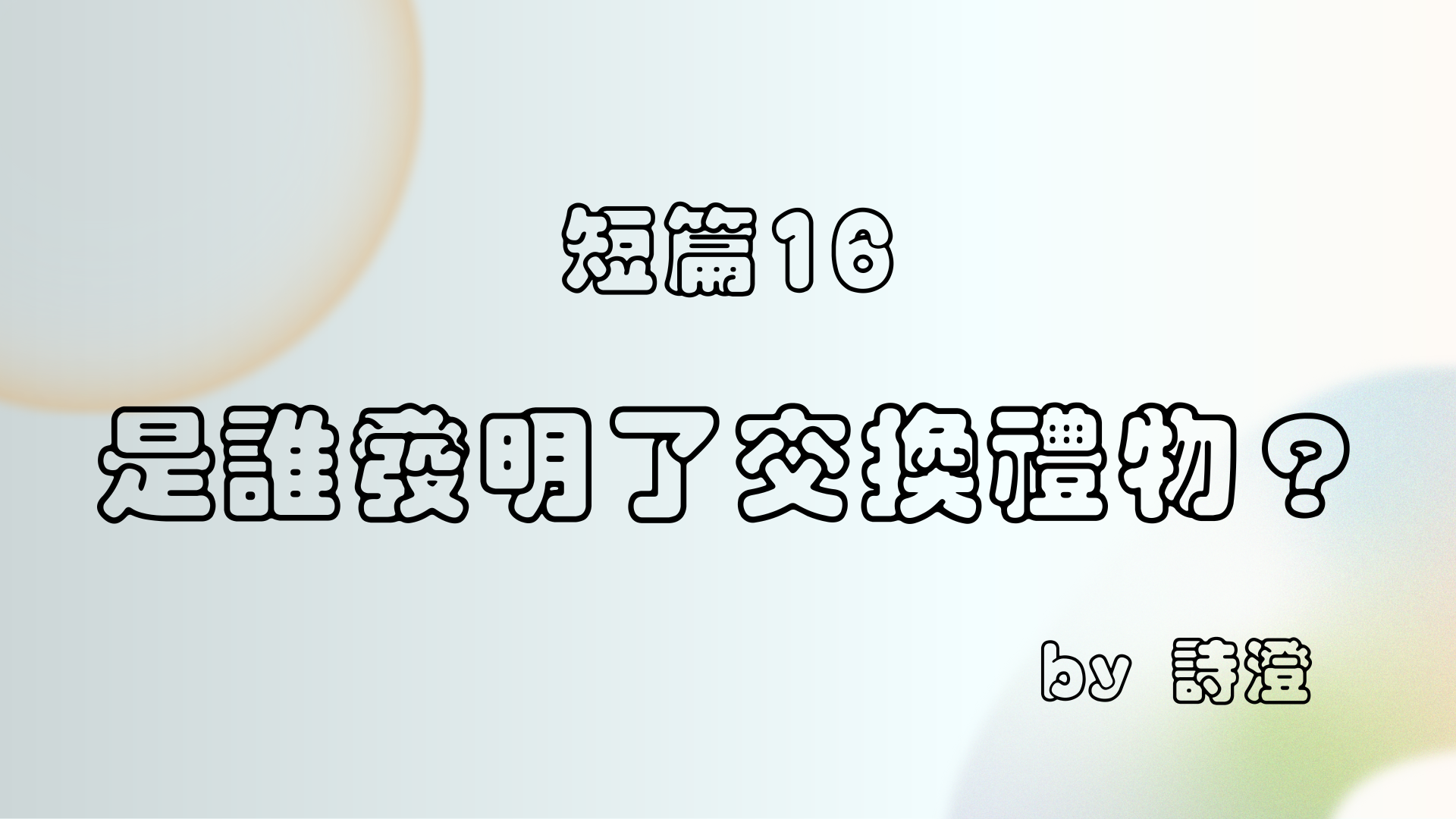我依舊傻盯着那一排鐵柱,不管是晴天、陰天或者是今日的雨天,我都風雨不改。每根鐵柱的表面皆已為褐銹所侵佔,代表它們在這兒立足已有數十年的時間,而我也在這兒望足了十年。
我知道我這樣傻呆着是沒有意思,也於事無補,但我又能作甚麼?短短三十多年的生命因一時衝動而付諸一旦,我從那時起已踏進通向地獄的不歸路,無法回頭。無論我向多少人道歉多少次,或跪地求饒,也沒用了,「對不起」這三個字在此刻顯得毫無意義,上帝早已把我遺棄在這裏。
每次我想到這裏,都會被另一個念頭狠狠地搧一把掌,想要提醒我我做了對得起自己的事,企圖安慰我的罪疚感。沒錯,艾莉這個婊子,背叛了我!我一直這麼深愛着她,待她如珠如寶,視她為我生命的一切。而她拿了甚麼來回報我?和那王八蛋共渡歡宵?哈⋯哈哈,我真是太天真了,竟然會幻想你會和我在一起,直到永遠?哈哈哈⋯
我跟著冷笑了起來,笑聲斷斷續續的,仿佛一個殺人狂在滿足他的慾望後那種得意的笑容。對呀,我就是那個殺人狂,禽獸不如、無恥、殘暴⋯⋯正因如此,我的弟弟不再親我,我的父母不再認我,我的朋友不再理我。我是一個無名氏,是人類的渣滓,是社會的敗類。我的生命不再有意義,相反它只會為我身邊的每一個人,不論和我的關係有多近有多遠,皆會掛上羞䎵的名牌。他們會以認識我為恥辱。
笑聲逐漸混和淚水,變得哭笑不分。我開始用力扯着我頭髮,同時用手肘輪流捶打在桌上,雙腳則在胡亂蹬踢。我想我是在懲罰自己吧。我越用力,我就越痛,我也就越自我感覺良好。要是有人從此處經過,他一定會認為我是個神經漢,而我也希望如此。要是有人經過⋯⋯?
一副高大的影子逐步靠近,然後停在我前面。果真有人經過!我抬頭一看,是獄長,他先用了很長的時間細心地打量着我,然後他以一貫的嘻皮笑臉問候我:「呵呵,你可真是個大人物呀!臨死前還有這麼多小學生來探望你,真令人羨慕⋯⋯」,他的眼睛甚至沒有去轉動一下,目光依然不肯離開我。
我甚麼也沒說,只是筆直地坐在我唯一的座位上發呆。獄長的話令我回想起昨天的事:一大群七丶八歲的小孩子來到我身邊,對我指手畫腳,又用他們的手指戳我、捅我,同時說些十分難聽的話,叫我快點去死。一旁的導賞員使用喇叭在我的耳邊尖叫,她說了甚麼,我已不怎麼記得,大概是那種說我是個奪去兩條性命的魔鬼,用怎樣殘忍的方式殺人之類的話吧,反正我也不是第一次被當作教材,去告誡那些小孩子長大後不要去學我了。
那些小兔崽子捏得我真痛,那種不愉快的感覺到現在還不能消退。在我想下意識地撫摸傷口的時候,獄長又開口了:「給,這是你的最後晩餐啦,好好地去吃,明天可是有幾十部攝錄鏡頭等着你,你的死刑將會是大新聞呢!連續數星期的報章雜誌都會有你的肖像!哎喲!還有那個可愛的慶祝嘉年華呢!多麼令人興奮啊!好好準備明天要對記者說甚麼吧!」他從鐡欄門下窄窄的空位塞進只有臉蛋那麼大的薄餅後,便笑呵呵地走了。我沒有多想便撲到那塊薄餅上,雙膝跪下,狼吞虎嚥地把它一塊塊地食下。我感覺自己像一隻狗,但我已有好幾個星期沒吃東西了,徹底餓透,誰還有這閑功夫去管甚麼餐桌禮儀啊?更何況這種姿勢才是在這連坐着也困難的牢房裏最方便自在的。
就像往常一樣,薄餅淡而無味,但總好過沒有,總好過隔壁的那位囚犯。我一直沒能知道他的名字,但我聽說他偷了人家幾塊銅錢,就被執法官判為罪大惡極,分配到這所監獄來。他關押的時間比我要長許多,曾有好幾次他被限制進食量,搞得好幾個月都只能喝清水;他的牢房小得要讓他被迫躺着,「食物」則是從管道灌進他的口裏,每隔幾小時便有水泵的嘩啦嘩啦聲,還有一種類似窒息的唔唔聲⋯,我忽然感覺自己比他幸運多了。
現在那位囚犯已經贖罪,可能已獲得上帝的寛恕了吧。那一天我是有份出席的,實際上所有囚犯都要出席,畢竟這是監獄裏的規定。當中發生的事,到今天亦記憶猶新,太可怕了:他躺在手術台上,四肢被天花板上的鐵鏈死死地栓住,動彈不得,機械的嘶嘶聲和隆隆聲則無休無止:一會兒跑來一把大大的曲線鋸,一會兒又跑來一根長長的切肉刀,然後就是撕心裂肺的喊叫,但他每一次的喊叫只會迎來更大的痛苦,而那些鮮紅的血漿也在不斷地噴濺出來,原本雪白的床墊都被完全地染成紅色。這不禁讓我想起艾莉和那男人不再動的樣子,我當時真想把雙眼緊緊地閉上,好讓我籍着一片漆黑來把我和外界隔絕,但我的眼皮被夾了起來,連眨眼都成問題,那種眼睛乾燥得像被火燒的感覺我仍然難以忘記。我被迫看着這個過程的全部,由始至終,一個不失。到最後我只看到一堆殘缺不全、血肉模糊的殘渣,完全認不出這堆破爛曾經是一個人。但當然,他早已不是「人」了。
之後連續幾個星期,新聞和廣播都放着他接受贖罪的錄影片段和音帶,在這些日子我都不能安睡。他空洞的眼神仿佛在每時每刻都在看着我,他尖銳的慘叫聲每分每秒都在我的耳邊重覆又重覆,他的殘骸丶他所剩下的一切丶他…他的身旁隱約出現了一個女性的身影⋯是艾莉嗎?艾莉?為甚麼是艾莉?只見她全身都披滿了鮮血,還帶有那種噁心的血鏽味,她奄奄一息地呻吟着,十分痛苦。當我正想上前去幫助她時,一隻粗壯的手向我襲來,死死地扣緊我的咽喉,想要置我於死地。一定是那混蛋!那個奪去我女人的混蛋!然而一切都要逐漸化作黑暗,我的感知也越趨模糊,但那混蛋樣子卻越來越清晰,好像真的是他!我費力地掙扎着,終算把那隻可憎的手甩開,但鮮血卻一下子掃到我的臉上,我甚至能夠從舌頭嘗到那股血腥的味道,空氣中飄來一陣屍臭味,令人作嘔。此時,我看見地上有兩件正在腐爛的屍體,身上有數百隻丶甚至是數千隻幼嫩又肥白的屍蟲在他們身上瘋狂開餐,貪婪地吸吮着他們的鮮血。那個男人死了,艾莉也死了,他們全都死了,情形就如當天一樣,而當天的恐懼感丶罪惡感丶愧疚感也再次全部佔據了我全身,他們死亡的過程還在不斷地在視線中重演…重演…
不要!我不要!我不要再回想起這一切!!我立即用手緊抱着頭,同時左右不停地翻滾着,盡力扯着嗓門大聲吼叫,好藉着難聽的叫聲將頭腦中這段噁心的記憶掩過。可是,我叫得愈久,我的聲音就愈沙啞,像洩氣的氣球一樣變得有力無氣,艾莉和那個混帳男人也趁機如潮水般再次湧進我的腦海。此時,那陣期待已久的電流隨著噼啪聲呼嘯而出,緊接着我全身上下都出現了劇烈的抽搐,肌肉緊繃得厲害,在縮緊和擴張之間不斷循環,好像隨時要被撕裂得支離破碎。每條神經線都在跟著我尖叫、哭喪,痛苦地掙扎着,眼前的影像終於不再是他們了,而是被各種顏色丶各種大小的斑點佔領並取代,猛力地閃爍着,每塊斑點都想要在視野裏爭一席位,它們愈閃愈快,愈閃愈快,愈閃愈快⋯突然,眼前一黑,甚麼東西都不存在了。
我又回歸到沉寂中去…我的腦海裏有無數幅畫面飛快地閃過:我的家人丶我的朋友丶我的敵人丶我的艾莉,再然後是我第一天進入監獄的情景:我的腦門被打開,將晶片插進去,從那天起艾莉和那個人便不斷地死去再復活丶死去再復活…我身處的那些黑暗的小監倉,難忍的臭味,和滿地的污穢物…我被教導成為一隻畜牲…我竟然相信了上帝…所有的影象都在高速旋轉,像走馬燈和萬花筒混合而成的亂像,然後一切都漸漸模糊起來。只有水泵的低鳴和囚犯的哀嚎還在提醒我其實是處於現實,其餘的早己化為虛無飄渺的幻象,統統被那兇猛丶深邃的漩渦吸進去,輾個粉碎,然後消失得無影無蹤⋯
最後的六小時在一秒一秒地過去,我也用盡了這些寶貴的時間逐字砌出我的遺言,大概是這樣吧:我是一名死囚,我的名字並不重要,因為我是一個泯滅人性的衣冠禽獸,而禽獸的名字是沒有意義的。我十分邪惡,所做的一切,人神共憤。我實在沒有資格存在於在這個世界上,而現在十年的苦行終於要來個終極審判,結束我毫無價值可言的生命,結束我只會害人不淺的一生。我必須死,才能造福百姓,上帝呀!我一直在等着你的打救,請祢接受這個污穢的靈魂吧!請祢寬恕我這個充滿罪孽的靈魂吧!!請祢打救我吧! ! !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