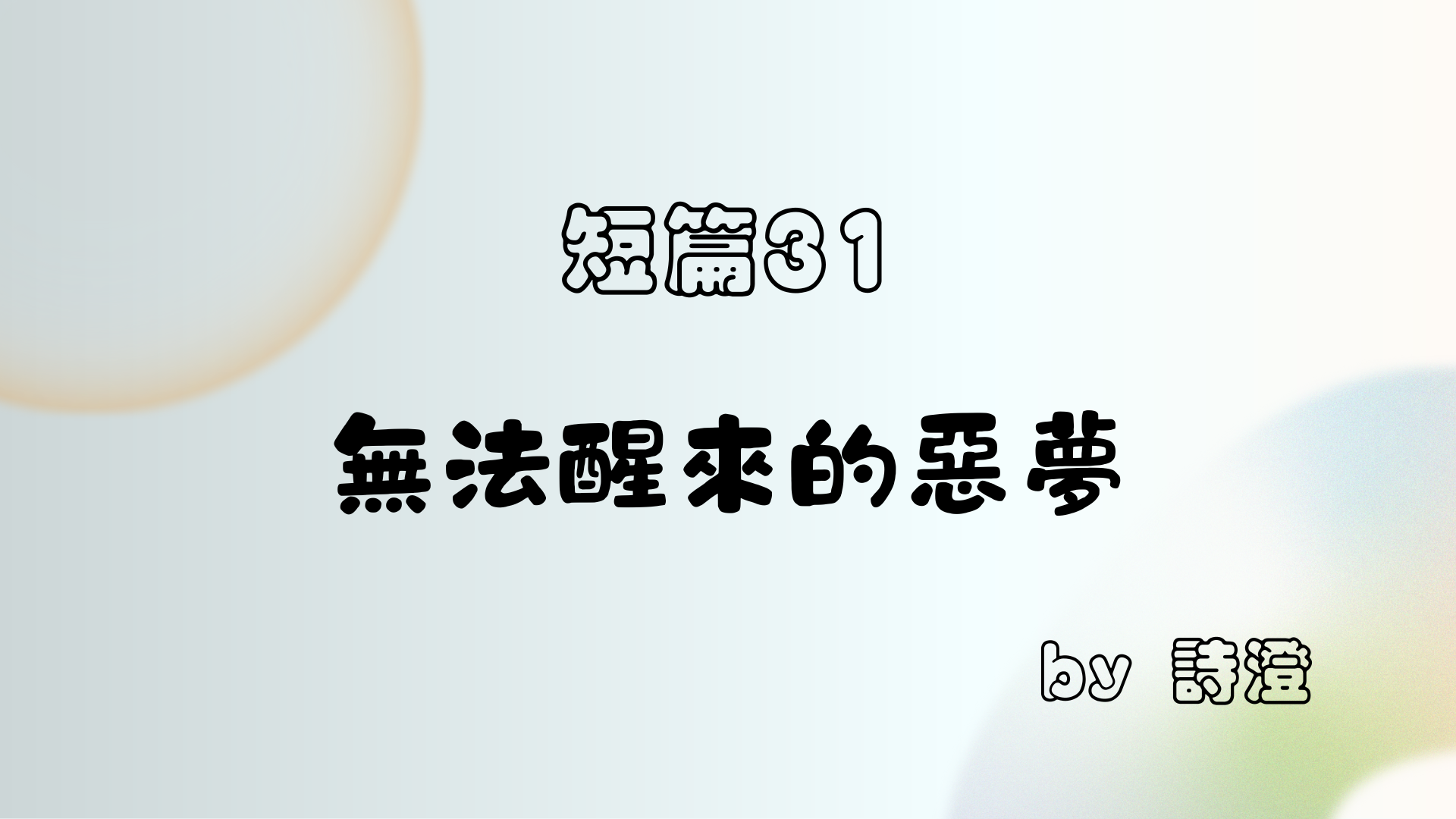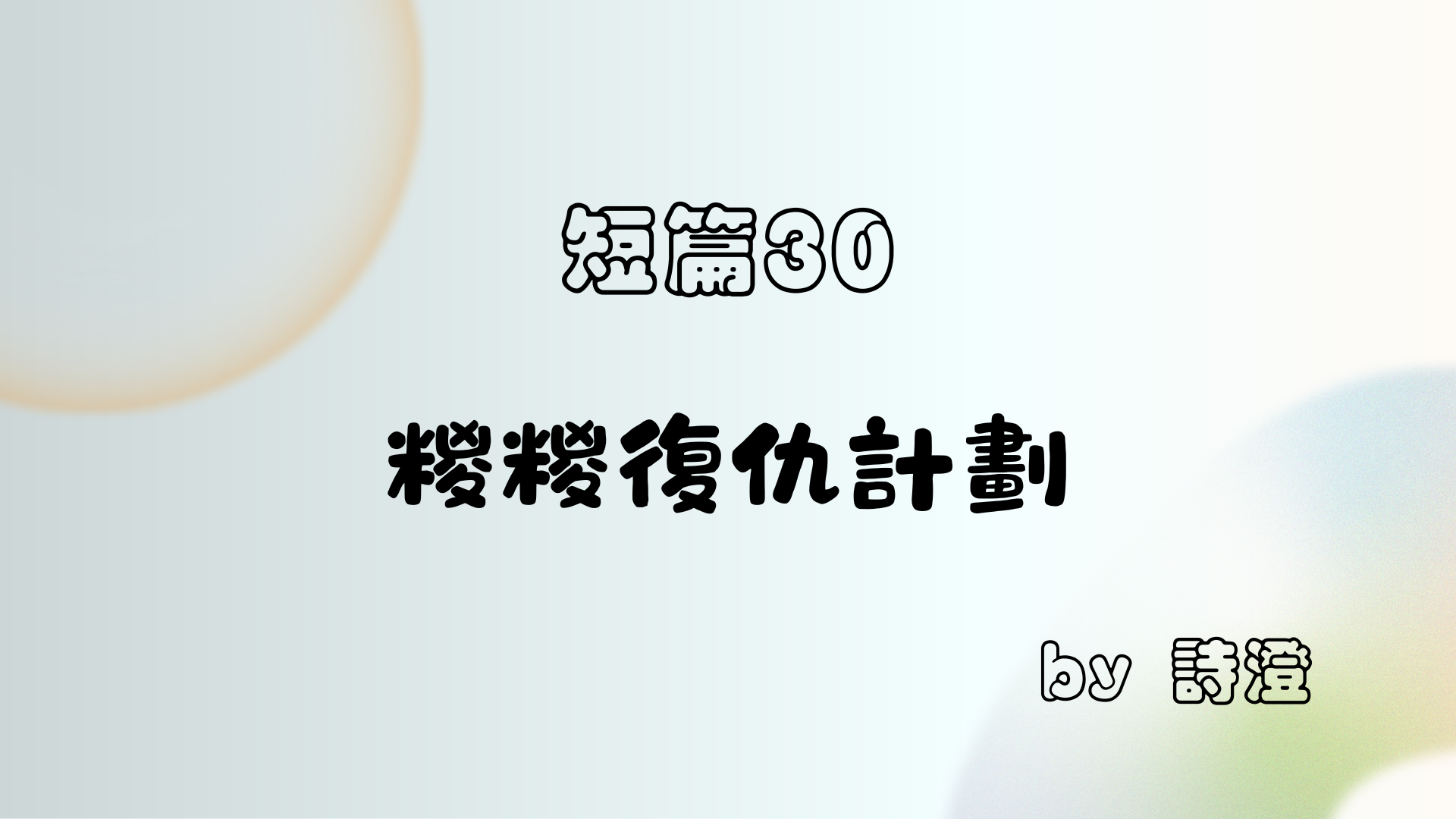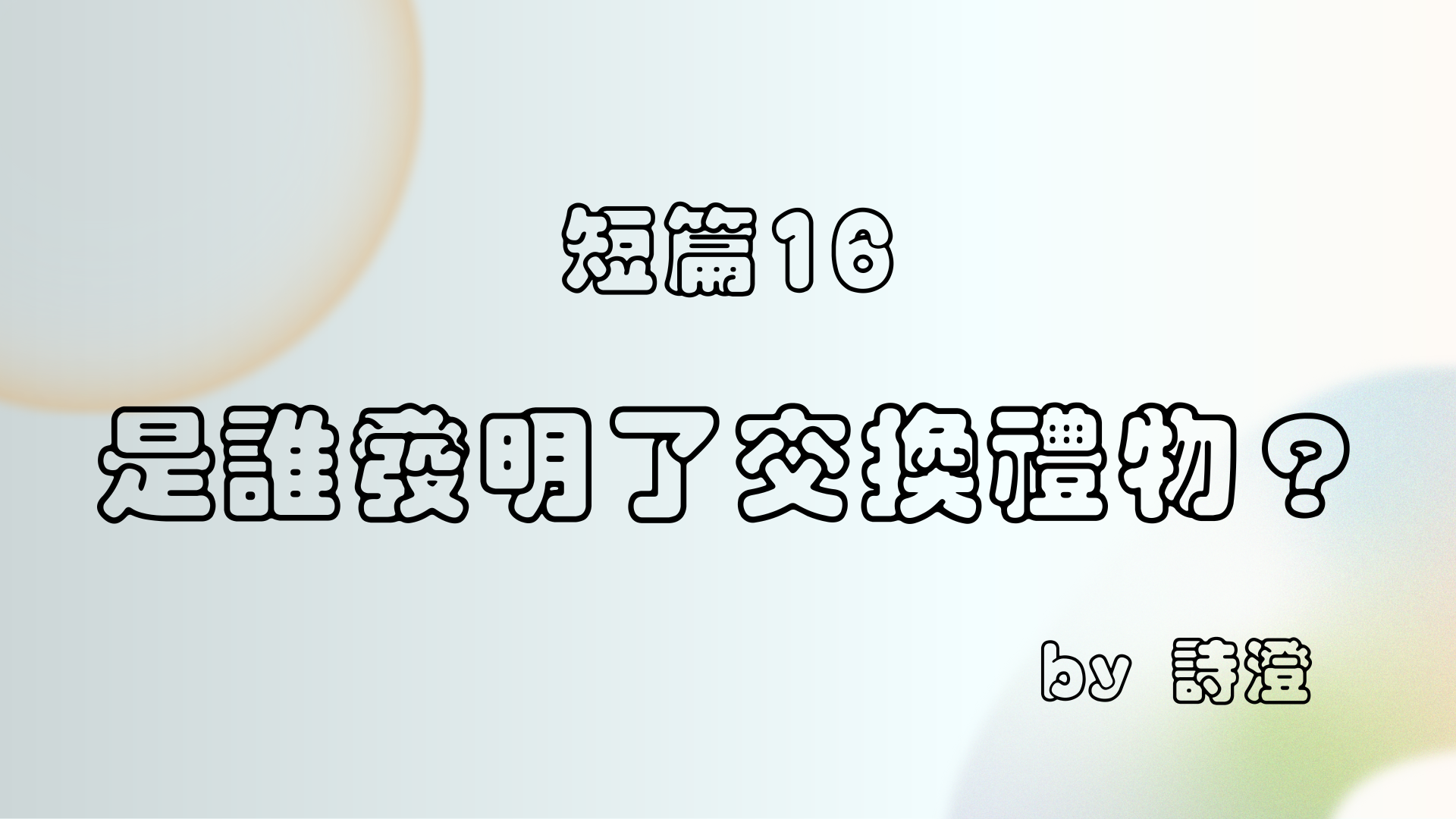為什麼?
我想了想為什麼,可能沒有確實的答案,儘管如此仍然盡努力去試著想為什麼。不過沒有答案的事才不會因為有問題而突然出現,情況猶如先有雞,抑或先有蛋的道理,純粹在乎個人的選擇。
人啊!當選擇了某一方的時候,便會變得固執,忽然間就變成一頭牛,變得蠻不講理。當然有一撮人不受上述影響,他們可以隨心改變主意,是典型的功利主義者,只要順著風向就好,但他們不是人,只是披上了人的皮囊而已。又或者他們本來是人,經過長年的磨蝕後,人的靈魂失去了,只剩下皮囊,而人的皮囊基本是一個優質上乘的容器,以致社會上逐漸充斥了許多披著人皮的什麼東西。
是什麼東西暫時還搞不清楚,可以肯定的是絕不是外星生物,外太空只是人類虛構、對心靈空缺的填補。人的靈魂沒有一個是完整,必須從外界許多形形式式的東西來填補,有人相信神,有人則相信科學,不論人們相信哪一方,終究都是不存在的,真正存在的,只有我們人類彼此。
真正存在的,我們反而不願去相信。
我啊!能分別誰是人,誰是披著人皮的什麼東西。比如你前面那個手抱著布小熊玩偶的小女孩 - 她不是人。你不相信吧?這麼年紀小的女孩子,為什麼不是人?為什麼靈魂已經被耗盡了呢?我跟你一樣不清楚原委,誰會知道她短短幾年生命度過怎樣的日子,我既不是社工,也不是上帝,這事情不用我理,亦不必我理。
就像剛才所說,固執的人,我們是有靈魂而且固執的人,選舉了相信就徹徹底底地相信。如此詳細說明更不是強逼你相信,你必須了解,我們才能談下去。
你說「你不放下刀,我們怎能談下去?」
你錯了!我們從一開始是因為刀才結緣,要不是用刀威脅你,你才不會老實站著不動,要不是有刀,你更不會聽任何一句話,所以刀是必須的,況且它是我相信之物。
順帶一提,我相信科學,神不可能用魔法令你老實站著。
「那只不過因為你不曾看見魔法,是你狹窄的視野蒙蔽了自己,世界是廣闊無邊。神和科學並非不可共存。」
「科學是人類頭腦知識的表現,它證明了人類是世界絕對的支配者。倘若神真實存在,祂的敵人必定比信徒多。
「事實是,無神論者只佔世界的一小撮。」
「錯了。真正一小撮的是相信全能全知的神的信徒,而絕大部份信奉的神,是以科學角度塑造出來能力有限的神。
能力有限的神?誰設定的限制?稍稍動動腦筋便知道當中的端倪吧?」
你想了想,放棄了無謂爭辯,是否支持神論,並不是當下最緊急處理。那把刀,那把真實存在的刀才是重點。別搞混了!
「你想得到什麼?」
人是貪婪的,而貪婪是必然的。每一個動作,每一句話語潛藏的暗語便是人心底無限的慾望,我們是因為慾望而生,最終亦會因為慾望而死,這是不爭的事實。
不過呢?我們都對慾望了解不深,正如你竟然如此笨拙地直接提問。
我很懷疑,你對生是否仍存有慾望?儘管現在的你可能驚慌得失了方寸,但本能是反射動作,最能直接表現慾望。我幾乎可以確信你對生沒有太多眷戀,之所以還活著純粹因為沒有死。
誰都沒有打算將我殺死(包括自己在內),你這樣想。
「當然是想得到滿足。」
生存很麻煩,死亡亦不見得比較簡單,不過生或死都不算最麻煩的事。最使人懊惱、費煞思量其實是「選擇」。
「我們的九點鐘方向,有一個頭髮染了深啡色的少女,你看到她嗎?」
你沿著我的指示,在不遠處找到那個身體正在顫抖的少女,她身後有一個戴鴨舌帽的魁悟男人,他的右手藏在少女的腰間背後,其動作跟我和你的狀態極其相似。
「來選擇吧!」
「選擇什麼?」
「我可以放你離開,要是你走了,那位少女會代替你死。」
聽到了那個少女可能因為自己而死,你再一次細心打量她。除了深啡色的頭髮,五官尚算標緻,身材中等,能表現出屬於女性應有的曲線,衣著平淡沒有太多花巧。得到現實的資訊後,你開始想像非現實的事。
她,應該很文靜很喜歡讀書,假日在家中畫畫畫,讀讀書便過一天。成績優異,家人從不擔心她的未來,亦得到老師的欣賞。直至今天為止,一直過著幸福的平凡日子。
不過,也很有可能完全相反。她是個天生的淫蕩女人,即使有了伴侶仍然會為求一己慾望而出軌。在父母師長面前裝扮優等生,實際她是崇尚力量的極權主義者。
究竟她是個怎麼樣的少女,你開始權衡彼此之間的生命價值。
你實在比我想像中遲鈍太多了,因此我找了個出血較少的部位刺了一刀,希望疼痛有助你思考。
「沒有一把合適的尺,可以量度生命的價值。」
你似乎明白刀刃嵌入身體的痛多於我說的話,始終沒有作出選擇,倒是出神在少女身上繼續胡思亂想。
「她出生於單親家庭,由母親獨力撫養。十二歲初嘗性交,十四歲墮胎,母親在她十九歲的時候死了。為生活她到酒吧打工,陸續與許多不同的男人交往,墮胎次數不斷增加,她就是這樣的人。」我給了你一個假設出來的背景,你半信半疑,傾向不相信,但思緒已經被動搖。
儘管對少女的印象有了壞的影響,可是卻對不作選擇堅定不移。既不希望自己死去,也不希望少女因自己而死,究竟你是悲觀,抑或過分樂觀?
人的生命不應有不同價值,人命是平等的,不分富貴窮苦,但人卻加以標籤化,是資本主義的極致表現。我討厭你的懦弱,討厭你對生命的價值觀。你憑什麼認為少女不值得為你而死,又憑什麼決定她應該活下來,既然得到了選擇權,為什麼不把握善用?這個世界並非由對錯組成,少女的家人或許會恨,而你或會被世界唾棄,但都不過是表面,大家始終會由衷地認同,否定純粹因為情感的需要,刻意保持善的一面,情願虛偽得令人舒服,也不要現實的磨折痛苦。
「我們三點鐘的方向,哪裡有個年邁的老人,他和少女之間,選一個活下來吧!」
你別個臉,沒去找尋老人的蹤影,然後開始自我催眠「那裡沒有老人,那裡沒有老人。」
「好好看著,那個老人是大學講師,深受學生愛戴。沒有生育孩子,有一老伴從小相識,也是初戀。」
「他們的生死不應由我決定。」
「沒有應不應該,只有機會有沒有來臨的時候,正如你的誕生,也不存在著應不應該的理由。
或許你這樣想,就當是一次意外懷孕吧!現在你必須決定墮胎還是生育下來。」
為加深死的印象,他提起鋒利的生果刀,刀刃折射出太陽的眩光,使人不能正視。在烈日當空的正午底下,身穿漆皮外套的中年男人雙手握著生果刀在半空中停留了兩三秒,然後垂直插進老人的頭顱,能用生果刀穿過顱骨絕不簡單,這是中年男人唯一表現仁慈的地方,他竭盡所能,希望老人只感受到一刻的痛,因為接下來要將漆皮外套染成鮮紅色。
「我想起第一次看動物記錄片,人類以旁觀者的角度拍攝獅子啃噬小鹿的情況,儘管利用特效模糊了血肉分離的影像,但足以深深憾動了我。
事隔了十八年,今天的畫面再一次憾動了我,而且今次沒有特效,更不是視像。他為我們真實地呈現,以最殘酷,亦最真實釋放慾望。他做到了,找回人性的基本,終於變成有靈魂的人了,而不是別的什麼東西披著人類的皮囊。」
「瘋子!你是個變態的瘋子!連一個無力的老人都不放過。」
「所謂瘋子、變態都是人們為自己不願面對慾望而強加別人的貶義,藉此打壓。愈害怕,就衍生愈多的貶義詞。
易服僻!人妖!戀物狂!都是典型將慾望妖魔化的例子!」
中年男人變回一個擁有慾望的人類,而慾望是無窮無盡,至今為止已經數不清他在老人身上用刀刺了多少回,血染紅了漆皮套,變成一幅生動的潑墨畫。人血的味道不腥,相反有一種甜味,我伸出舌頭像蛇一樣試著舔空氣中含有的質感,終究什麼都感受不到。
「而且,是由你選擇的。」
「我沒有選擇。」
「你無可否認。」
「我只是受到威逼底下作出選擇,要殺死誰根本不是我的主意!」
「不過是文字上的形式改變,老人在物理上當然不是由你殺手,但老人卻因為你而死了,這點你承認嗎?」
「不!不!不可能承認,絕非我本願!」
「你不覺得自己的辯詞毫無說服力?我只是提供選擇,而你是選擇的一方,並且剛才作出了選擇,怎能夠反悔否認?
你可以感到歉疚,但不可以不承認。假若連你都否認了,那老人的死到底為了什麼?
「你是殺人兇手,法律自有判斷!」你放棄爭論,斬釘截鐵的執意偏見。
為了餘生不必感到歉疚,同時將我的形象妖魔化,企圖令自己在該事件中站在無人可質疑的道德高地上,不必受任何人指責,甚至可能得到某程度的讚賞,從而生活得輕鬆。你是個充滿矛盾的人,對活沒有概念,對死也沒有,不過硬要選擇的話你終究希望活下去。活著很難受,但死可能更差,況且經過二十多年了,好不容易才習慣生存,要是死了又得花上好幾十年去習慣,你可受不了。
受不了了,受不了了。
「我想問一句,你了解法律嗎?你清楚法律如何保障市民嗎?抑或只是你單純認為法律代表正義,而正義站在你那一方嗎?」
「正義不會偏袒任何一方,正義只會制裁邪惡。」
「為什麼邪惡必須被正義制裁?因為正義是多數的一方?抑或有什麼強大的理由?比如利益?
人啊!所有共識都是建基於利益上、價值上。縱使生命是無價,但幾乎沒有人真正認同。少女和老人之間,大家都會選擇少女,然後少數人會問及兩人的背景再選擇,更少數人會以叛逆的心態或自以為別樹一格選擇相反答案。
結論代表正義的法律,最終不過是維護人類利益的工具。
若以最簡單的例子比喻,為什麼人殺人需要受法律制裁,而殺死動物卻不用承受後果。
同樣是生命,同樣被弒去,而正義卻只為人類伸張。」
潑墨畫已經完成,一朵朵色彩鮮艷的紅玫瑰各有性格地綻開,象徵慾望的盛放,人們不再需要掩飾自己的感情,以及一個赤裸國度的誕生,哪裡有被人命名為阿當和夏娃的初代人類,帶領人們回到最初最率性的伊甸園。
圍觀的人們被這幅驚世的畫作嚇呆了,也無法理解當中的象徵意義,或是逃避不願面對真相。沒有利益的純真國度,簡直不敢想像是怎樣的一個無聊國度。既不能花錢買女人的身體,也不能肆意差遺工人。沒有手工細膩的服裝,更沒有舒適平穩的汽車,這個國度不可能適合人生存。
太可笑了。
太可怕了。
人們狼狽地逃竄,已失去的生命不能挽回,逃走並不是誰的錯。錯的不是自己,是他!是什麼東西!正義會制裁做錯的人,可惜的是正義不能夠在錯誤發生之前施以制裁。
唯獨一個膽大的青年仍在用新款推出的手機拍攝殺人畫面,同伴向青年展示身上的潑墨畫,像個表演時裝秀的模特兒。鎂光燈閃爍下,這世界竟然變得有點不同。
人啊!開始變得更像個人!
同伴背著老人的屍體,絲毫不理會緊隨其後的年青人,搞不好正在網上直播。於我們而言,並沒有什麼壞處,警方會透過視頻追蹤,而他離開的目的正正是分散外界的注意力。
「我們把握時候作下一個選擇。」
「我不會再選擇誰去死了,要殺就殺死我。」
「不要隨便說『殺死我』,你沒那種資格,也不在選擇範圍之中。
在電話簿中選一個致電,內容隨便你決定,限時一分鐘。」
「隨便我決定?」
「這已經是很明顯的提示了,有必要問得清清楚楚嗎?
如果你想向誰求救,就儘管對誰說,這樣說你懂了吧?」
你不是不懂,只是不敢相信,或是害怕相信。即使我清楚說明了,卻因為彼此的陌生關係,或已進一步的關係 - 施害者和受害者 - 而產生疑慮。你認為我一切的行動基於惡而為,正因為你對我的不了解,亦不願理解才誤會我。
你把電話簿內的聯絡清單重複看了幾遍,每一次都加重了憂慮,無法從眾多人名中挑選一個。甚至連談話的內容都未能決定,所以才久久不下決定。
我不能無休止地等待下去,唯有加上一個小小的時限。你變得更焦慮,手指在手機螢幕上滑動的速度不斷加快,這不過是焦慮導致的反射動作,視覺早已跟不上滑動的速度,你心裡已經有底,只是打算猶豫至最後一秒。
最終。在最終的一秒,你選了一個心底答案以外的名字。當下連你自己都訝異脫口而出的名字竟然是他。
我撥打那個名字的電話,在接通之前交到你手上。
撥號在你把手機貼在耳邊之前接通,一把熟悉的低沉聲音向你打招呼。在猶豫之際,我幫了一把讓你的手機靠到耳邊。
「什麼事?」
「你想知道什麼事嗎?」
「你姑且可以說,我姑且可以聽。」
「我不知道應不應該說,也不知道你相不相信。」
「應不應該說我無法替你決定,但我會選擇相信。」
「好吧!或許你會覺得荒謬,但這是事實,我希望你真的相信…」
隔了一會,你一直沒把話繼續說下去,在說服對方之前,卻無法說服自己。
「我希望你真的想說。」
「對不起。」
對方沒有回答什麼,直接掛線了。我嘆了一口氣,感覺有點失望,難得給予你一個絕佳的機會,卻只有草草幾句說話便完結了。沒有內容,也沒有感情,彷彿是個兩個機械人運用預設的句子交談。
你也嘆了一口氣,從表情來看是輕鬆的、坦然的,平和的。
「你這是幹什麼?」
「按你的要求致電給誰,不是嗎?」
「就這樣已經足夠?」
「權力 - 就是你追求的慾望吧?總是想左右別人的決定,才想到這種惡趣味的選擇遊戲。
嘴巴說什麼崇高的理想,不過就是個人對權力追求,你的同伴也不過是踏腳石。伊甸園只是代號,你真正想建立的其實是一個帝國,而你想成為帝國的君王。
不過現代社會有誰想成為帝國的君王是絕不可能,正大光明的獨裁國家太受矚目,經歷過數千年的殘酷戰爭,人們已經將道德升華至至高無上的地位,並且將平等掛在嘴邊,儘管道德和平等都不過是虛無的表象。
「了不起!了不起!你猜對了,伊甸園什麼的怎麼可能存在,這是個道德至上的虛偽世界,然而道德的原意已經完全偏離了原來的軌道,也成了攻擊他人的大殺傷武器。
道德是高牆,許多人自以為站在高牆上,便可傲視牆下的無恥之徒。可惜通通都搞錯了,道德並不是高牆,而是泥沼,這是真正站於高地上的統治者所設下的陷阱。
獨裁的統治從古至今一直存在,只不過是形式上轉換了。世界上有數之不盡的人身不由己地活著,不納入其中的,便是統治者一群。
一個分了上司下屬的階級社會,一個如此鮮明的帝國縮影,到底是人類傻得不了解,抑或選擇沉默地接受。
起初我真的想建立伊甸園,不過在過程中搞清楚了一件事。人啊!因為擁有感情和性格,所以分成了不同種類,並不是世俗那種以膚色或性別畫分,而是以主導、被動和自由三大因素區分。
主導和被動之間最大的差異在於創造性;被動的人欠缺創造性,無論如何優秀始終需要依靠前人足跡,遵從舊有的道路而行,活在既定的框架下。這沒有什麼不妥的地方,人只要活得舒服便可以了,並不需要每個人都擁有創造性,相反創造過多的東西更容易令社會混亂。
「簡而言之,大部份的人希望被統治。比起必須創造什麼所帶來的煩惱,被統治所受到的壓力反而較少,服從是相對一件簡單容易的事。」
「如此一來便能滿足各自的慾望,某程度也說得上是個伊甸園,你就沒有憧憬嗎?」
「別開玩笑了,只不過是以大眾的名義爭取個人的私慾罷了,連施捨也談不上,純粹不小心或無可奈何給予了大眾一些小恩小惠。」
「以一個主導的角色,你表演得太超過了。以你的力量,做一個被動的人會比較適合。所以,我們繼續玩遊戲吧!朋友和少女之間,選一個去死吧!」
這次你馬上意識到所謂朋友的意思正是剛才致電的那位,即是說我有辦法能殺死你的朋友。
問題就在於,相信不相信。我真的有能力殺死你的那個朋友嗎?沒有任何依據可以推敲,不受判斷左右的決定,純粹不希望誰死去的選擇而已。
按道理,按個人情感,放棄少女的生命是正常選擇,卻不容易說出口。那名少女就在眼前的不遠處,曾在老人和少女之間作出選擇,某程度上你和少女的生命之間已經混雜了些許。當然你原本的生命和那名朋友生命亦有混雜的地方,然而隨著時間的過去,即時的連繫比淡化的感情更真摰。
你竟然猶豫,慢慢開始說服自己去幫助少女。
「你沒可能知道他的住處,而且只是隨心選擇,我們彼此之間有好一段時間沒聯繫,我不相信你能如此神通廣大。」
「判斷並不重要,想法才是重點,到底你會對誰見死不救呢?」
「已經說過了,我不再會做任何選擇!」
「不選擇本來就是選擇的一種,若以表意的解釋,即是兩個人的死活都不在乎。」
「根本就不由得我選擇!」
「所以你就不選擇了嗎!!!!!!!!!!!」
少女滿淚盈眶看著我們,抖動的嘴巴開合著,似乎想要向你傳遞什麼訊息。不管你或我都沒有真正了解箇中意義,只憑各自的猜想選定心目中的答案。人啊!其實不存在誤會,只有一廂情願這件事。
在各種程度的意義上,你的朋友死了,不明不白的死了。究竟少女於你而言是否一個特別的存在,你開始產生這邊方向的迷思。
搞不好她是你命中注定的人,又抑或是上一世欠下的債,許多你原本不相信的神怪傳言,當下竟然一一認真思考有否關聯性。
「我很滿足,因為你,我確信有成立伊甸園的價值。」
「你會遭到報應的!」
「人啊!因為自身力量不足,便會依賴神力來尋求心靈上的慰藉。不是為了報仇,而是為了自己仍有動力活下去。
你不覺得,人許多的行為均以活下去來做前設,甚至求死的真相原來也是為求生。我愈來愈懂,愈來愈明白,果然有創造的價值,同時很感謝你們三位。
時間已經差不多了,我們來做最後一次選擇,你的答案將使我重新認識這個世界。
你的命和少女的命,到底誰可以活下來?」
「在選擇之前,我可以問一個問題嗎?」
「儘管問,非常樂意。」
「她剛才也做了相同的選擇嗎?」
「你想知道嗎?」
「請告訴我。」
「她是個很單純的少女,一心只想著情人,在電話裡講了幾句深情的對白之後,本想著默默離開,最後還是狼狽地向對方求救了,哭得一塌糊塗。
我特別提供多一個選擇給她。在自己,情人和你三人之間選一個活下來。她知道後竟然不哭了,還馬上決定自己生存下去。嚇一跳吧!大概是她終於覺悟,終於意識到自己的生命受到威脅。」
「果然是這樣。」
「果然是這樣?」
「她曾對著我們說什麼吧?我一直很在意她想傳遞的是什麼訊息,本來猜想應該是『救我!救我!』雙音節的語句。不過現在想清楚了,她不是說救我,而是說去死。
去死!
去死!
去死!
去死!」
「所以你會選自己活下來吧?」
「不,就讓她活下去。我已經完全失去了生存的基本慾望了,不知怎地覺得肩膀的重力消散了,身體亦因此變輕,這種輕鬆的感覺記憶中從來沒有過,卻又很熟悉,估計是嬰孩時期散失的記憶。
很感激你刺了我一刀,那一刀使我感受到死亡前帶來的疼痛。如今,我相信自己可以承受得到。以前會對生死產生矛盾,是因為對死還不太了解。被動的人總是喜歡選擇簡單的方式,從誕生以來,我們就被教導成如何在社會生存下去,而且刻意不提及死亡。
原來死才是最簡單,只須要無情的一刀,生命便會悄悄地無聲逝去。相反為求生存,折騰勞碌不停地工作,得到的竟然不是最直接的食物和住處,而是金錢,實在看不出那個地方簡單。
人被開明的路蒙蔽了,從而遺忘了旁邊有一條幽靜小徑。」
「我開始捨不得你死了,可惜規矩定了下來。」
「主導與被動以外的第三種 - 自由者 - 即是死人,對吧?」
「社會啊!要不你去約束誰,不然就是被誰約束,這正正是社會的作用,必須擁有規律,生命才可以循環。
我也不敢肯定死亡後會到自由的世界,對死的認知實在太少,因此才有空間給予寄望,就讓我們儘管將死包裝成一件美好的事情,反正不會有人有答案。
那麼,如果你真的到了自由的世界,請告訴我。」
咔嗞。
嗄…嗄…嗄…
…….




-01.png)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