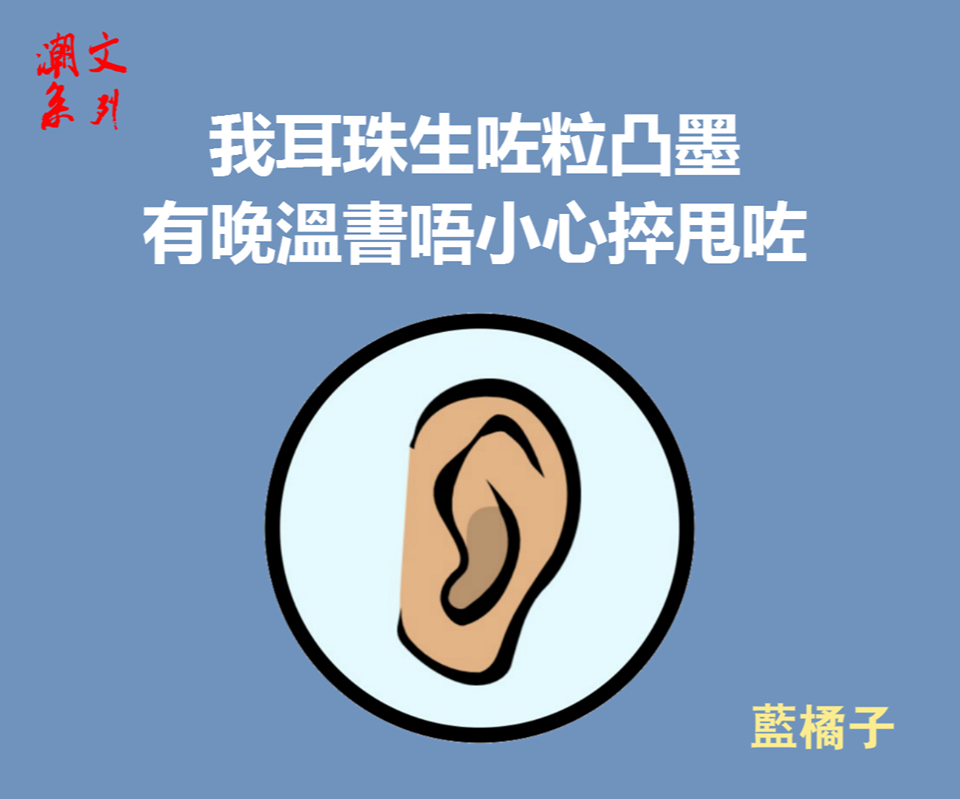聽到台上大聲呼喊自己的名字,緊接而來的是如雷貫耳的掌聲,羅伊從座位上站起來,輪座的醫生紛紛握手道賀,他低頭調整一下自己的西裝,背脊挺直地走上台。他接過主持人遞給他的獎座,獎座感覺很有重量,當然,它是素有美國的諾貝爾獎之稱,自 1946 開始的年度獎,所對醫學界作出重大貢獻才有機會得到它。羅伊牢牢握實它,這樣做就不會被人發現自己的手在顫抖了。眼看著這個拉斯克獎(英語:Lasker Award),他花了多年心血研究總算沒有白費,獲得這個腦海裡早就準備好的謝詞忘記得乾乾淨淨,草草向家人、妻子和一同研究的醫生朋友道謝,說了幾句榮幸能為世界作出貢獻之類的說話,羅伊就只能在台上呆著了。主持人很識趣,看見這個情況便立刻進入下一個環節,大會特地邀請了被曾經被羅伊的藥救過的病人上台,每個病人都很感激他,逐一跟羅伊握手擁抱之後,主持人將咪高峰交給幾位病人,他們走上台中央,對台下的所有醫生學者說出自己被這藥改變人生的經過。
羅伊所發明的藥命名為「天堂」,本意是讓一些患有絕症,或者臨近終老的病人服用,目的是讓病人產生強烈的迷幻感,將快要離世的絕望感覺一掃而空,或讓病入膏肓的絕患者重拾生存的希望。由於藥性過於強烈,每一次的劑量只有50微克,大約相等如一粒沙子重量的十分之一,甚至更少。這藥物現在美國的醫院都很流行,但基於安全或人道的理由,需要病人簽字同意的情況之下才能使用。由於這藥物非常危險,一旦劑量稍微出錯便隨時能致命。所以每次有病人需要使用「天堂」,都需要等羅伊親自為病人用藥。而今天,羅伊來到位於市中心的醫院,替一個正在「等死」的老人下藥,這老人名叫阿森,在早上正式簽名同意使用「天堂」,因為他說昨天夢見自己快要死了,所以一定要在臨死之前下藥。羅伊利用純熟的手法,將正確的劑量注入針筒,然後射進阿森的體內。不消一會,阿森緩緩閉上雙眼,眼皮微微跳動,羅伊檢查一下他的心跳和脈搏,就知道「天堂」的藥力正在發揮,他開始進入夢鄉了...
「爺爺~爺爺~」阿森的耳邊傳來小孩的吵鬧聲。
「咦?是你?怎麼會...」阿森瞪開雙眼,眼睛環顧病房周圍,還是熟悉的病房,令人討厭的藥水味,不是說有人要來用那種叫「天堂」的藥嗎?怎麼現在全不見人了?
「爸爸,我很想念你...」站在床邊的,是阿森的女兒,而兩個吵鬧過不停的小孩,正是阿森的孫子。
「......」是夢嗎?阿森皺起眉頭,因老人病住院已經幾年了,女兒跟那個男人結婚就從來沒來探望過他,現在怎麼會突然出現?
阿森用力撐起身子,打算坐起來,女兒趕緊扶住他,然後把病床調高。阿森坐在病床看看她的女兒,又看看向著他傻笑的孫兒,然後視線轉向放在床邊的儀器,儀器不停發出煩人的「嘟、嘟、嘟」聲。他還凝視插在手臂及身體上的喉管,刺在手臂的喉管使他癢死了,滿是不協調的東西陷進身體內,好不舒服。阿森確認這一切都是真實之後,再次望向已經很久沒見過面的女兒,女兒哭著說對不起。「傻瓜,我根本就沒有怪責過妳啊...」阿森安慰她。阿森用充滿皺紋的手替女兒擦掉角眼的淚光,就在這個時候,他的主診醫生走進來了,兩個孫子歪著可愛的腦瓜看著醫生,是小孩子害怕醫生吧,真是可愛啊,阿森的心情慢慢好起來。
「喂喂!我早上不是簽名用「天堂」了嗎?」阿森用怪責的語氣看著醫生說道。
「的確是,但因為先生你的病情有變,所以想再跟你確認才決定使用。」醫生古板的語氣一直沒變,阿森再次確信這不是夢了。
「病情有變?」阿森其實不感驚訝,他一直被關在這裡,每天吃著不知名的藥,搞得沒胃口,連小尿都有陣陣藥味,定期的腦波檢查、心電圖、驗尿、抽血,每次報告一出來都是看著醫生搖搖頭,阿森連自己也知道死亡將至。
「沒錯,很奇怪的,上一次的報告出來了,你的身體開始迅速地恢復過來了,連舊患和一直糾纏著你的惡性腫瘤也離奇地消失了。」醫生像翻譯機一樣,將內容不帶感情地讀出來。
「什麼?」阿森難以置信,深呼吸一下,的確內臟不再痛了,而且四肢也感到力量飽滿。他看看女兒,女兒高興得又開始哭了。
「醫生,那麼...」阿森眨眨眼睛看著醫生,連近視和老花都消失了嗎?真是奇蹟...
「沒錯,你隨時可以出院了!」醫生高興地拍掌。
阿森高興得在床上彈跳起來,兩名孫子不知發生什麼事,也跟著高興地手牽手團團轉圈助慶。阿森自行拔掉身上的喉管,猛力扔在地上之後,便牽著女兒步出醫院了。女兒問他最想去那裡,大吃一頓嗎?回家?還是去拜祭母親即是阿森的妻子呢?他想了半晌還是拿不定主意,也許是沒想過自己有出院的一天吧。驀地,阿森一手牽著女兒,另一隻手,伸出粗大的手指讓兩個孫子握著,便邁步向前,撇過頭微笑地跟女兒說:「我們去遊樂場吧~」
當時是十二月的寒冬,周圍的景色看起來帶有冰冷感藍色,天空一片通透,阿森在醫院就被這種天氣弄得好幾次發高燒。現在他雖然衣著還是住院時的衣服,但絲毫沒有寒冷的感覺,身體像個暖爐一樣暖烘烘的。相反女兒纖幼的手就顯得冷得像冰條一樣,阿森緊緊包裹著女兒的手,讓她可以暖一點。到了遊樂場,孫子們支箭般向著機動遊戲衝過去,其實阿森就對那些遊戲興味索然,只是一味坐在旁邊的長椅上傻笑。就這樣呆坐著一整個下午,夕陽斜斜地灑落在整個遊樂場上,放眼望去,孩子們拖著細長的影子在互相追逐奔跑,連絡不絕地拉開嗓門喧鬧著,即使閉上眼睛也感受到歡樂的氣氛,原來快樂就是這麼簡單。阿森在自我感嘆著,望向坐在旁邊一直微笑著的女兒,橙紅色的光線剛好照射在她的臉龐上,她甜笑的笑容就跟小時候一模一樣,好美好美,赫然一股幸福的暖流從丹田處升起,對啊,幸福就是這麼簡單...
「感覺,好幸福啊...」阿森突然冒出這句羞臉的說話。
「對不起,之前一直忙於工作,結果又生了兩個小孩,把你忽略了。」女兒的聲音像蚊子般小,但卻清晰地貫進阿森的耳裡。
「沒關係,我明白的,妳長大了...」阿森撇過頭望著遠方,免得女兒看見自己的眼眶中滿是打轉的淚水。
「父親,我好想你...」女兒突然雙手攬住阿森。
「我也是啊...」身驅一動,眼淚落下。
「嘟~~~~~~~~~~~~~~」突然一道長響的聲音在耳窩裡發出。
「咦?」阿森嚇得膛大雙目,他認得這是討厭的醫學儀器的鳴叫,為何會在這裡出現?還有,這個長響不斷的聲音,不是代表...
「可惡啊...原來是夢嗎?」阿森看著周圍的景色像被火燒的蠟燭一樣漸漸溶化,攬住女兒的觸感也變得虛幻。
「再見了,女兒...」阿森嘆了一口長長的濁氣,緩緩閉上眼,感受著最後殘存著的幸福感覺。
故事完結了,台下再次報以掌聲鼓勵,羅伊在旁聽著也感動得眼角泛起淚光。腦海中浮現出當時瀝瀝在目的畫面...咦?等等,剛才不是說這個老伯已經死了嗎?怎麼又能夠在這裡跟大家演說故事?羅伊望著這個老伯,他確確實實地站在自己面前啊,而且我還有幫他用藥的記憶,沒可能錯的,難道是我記錯了另一位病人?羅伊一臉困窘,主持人又立刻請來另一位病人,他是一名二十出頭的少年,名叫木村龍太,是日本人,他的衣著前衛,將頭髮染成鮮紅色,瘦削的身體後還背著一個大吉他。羅伊記起來了,這個叫龍太的青年是差點因錯誤服藥而斷送生命的人啊,幸好最後來得及救他,不然就浪費大好前途了。看著龍太拿著咪高峰的架勢,應該仍有在努力唱歌吧?
在龍太畢業後,還沒寫第一份履歷,就背著結他尋找屬於自己音樂的夢想。他離家出走後一直將自己錄製的Demo親自送去唱片公司,但幾乎沒有演唱經驗的他當然會被唱片公司拒諸門外。龍太沒有放棄,他跑到酒吧裡開始他的演唱生涯,這一唱就是五年。他一直努力地寫歌、作詞、唱歌,總希望有一天能受到唱片公司的人賞識,酒吧裡的同事和老顧客都覺得龍太是個充滿熱血的青年。雖然酒吧未免有點污煙濁氣,但他堅絕不煙不酒也不沾上毒品,任何會影響他歌唱事業的東西他都不會碰。
他就一直過著這種守紀律,又有點反叛的演唱日子,在酒吧裡除了有些固定來酒吧聽他唱歌的顧客外,龍太還自己做了一個網站,前來留言的支持愈來愈多,這些都是龍太一直堅持的動力。除此之外,龍太還用歌聲來結識了現任的女友,她名叫菜菜子,是龍太的忠實歌迷。但拍拖一年後,還是敵不過生活的逼人,菜菜子想他放棄音樂,踏實地找一份工作,為兩人的將來打算。雖然龍太也很愛她,早已認為她是伴隨一生的人,但音樂是龍太的夢想,最後他還是決定了跟菜菜子分手,繼續他的音樂之旅。
有一天,他感到身體有點不適,總是咳過不停,所以他跟酒吧請了幾天病假,打算看醫生後好好休息,養好嗓子。但結果,他患上的不是一般的感冒咳嗽,而是能奪人性命的癌症。龍太聽見消息後的心情猶如晴天霹靂,一直熱血樂觀的他,怎樣都無法接受這個事實。有這麼嚴重嗎?當時他深呼吸一口氣,肺部微微刺痛,氣管有種被梗塞住的感覺一樣。但,這種微微的痛楚竟然是患上癌症的病徵嗎?後來醫生勸龍太不要再上班了,還替他介紹社工協助,希望他可以盡快通知家人。社工?自己患病了,幫助自己的不是醫生,而是社工?患者明明快要接受死亡了,還口裡一直嚷著叫傷心啊要積極生活啊之類的廢話,這種人到底對自己有什麼幫助?
拿著報告書回家的途中,龍太一直想不通,一向不煙不酒生活有規章的自己,怎會患上這種令人絕望的病症。酒吧裡吸毒成癮的大有人在,但他們仍然活得好好的,相反自己卻...為何上天要這麼不公平呢?咳、咳咳...龍太又咳嗽了幾下,鼻子彷彿嗅到從肺部吐出來的混濁味道。另外,當年一聲不響就離家出走這麼多年的他,應該怎樣將這個消息告訴父母?現在龍太的感覺,就好像個一向都會努力學習溫書的乖學生,結果考試卻拿了零分,考慮應該怎樣告訴家人的情況一樣。
感到絕望的龍太隔天回到酒吧,用他所有的積蓄跟販賣毒品的人弄來了「天堂」這隻藥,聽說這種藥能令人一瞬間達到夢想呢。雖然聞說這種藥很危險,一旦錯誤服用的話就會有生命危害,而且沒有醫生的情況下服用還是非法的。但這些都沒所謂了,龍太一生循規蹈矩換來的是什麼?這次就讓自己放縱一下吧...針筒刺進手臂,將冰冷的液體灌進體內,龍太感覺到液體快速竄到身體各個部位。他一直低頭看著自己的身體會有什麼變化,突然他看見四肢開始使不上勁,然後像被火燒的蠟像一樣溶化,然後是身體,最後整個人連思想都變成了可以隨意改變形狀的液體,開始了嗎?就做個成為歌手的夢吧...
接著,再次睜開眼睛的龍太,竟然發現獨自一人在酒吧裡的台上睡著了,不是說要做歌手嗎?怎麼又回到酒吧了,還空無一人呢。龍太從地上站了起來,發現自己背著陪伴已久的結他,深呼吸一口氣,肺部的梗塞感消失了,嗓子發聲的力量還很紮實飽滿。這時他發現台上坐著一個人,仔細一看原來是菜菜子,她是龍太現在唯一的觀眾。這讓龍太回想起來,在跟菜菜子分手之後,有幾次發現她偷偷來酒吧找了個幽暗的位置坐下來聽他唱歌,儘管菜菜子不支持龍太繼續在酒吧唱歌,但還是很喜歡聽到他的歌聲呢。
在我夢裡出現的竟然是妳嗎?想不到在我的心目中,你比起成為歌手的夢想更重要呢~
在台上看著菜菜子,龍太心裡感到有點愧疚,當年應該跟妳一起生活的,真對不起啊...不過現在也沒法子了,就讓我來最後一次為妳演唱吧~
故事說完了,龍太向台下躹了個躬,也跟羅伊握一握手,說感謝令他尋回自己真正重要的東西,現在龍太跟菜菜子已結成夫婦。羅伊心裡奇怪,不是說患了癌症嗎?非法服用「天堂」的人,怎麼會出現在這個醫學界重大的頒獎禮上?沒有人理會羅伊心裡的疑惑,龍太即場為大家獻唱一曲,台上的人包括頒獎的主持人一起隨著節奏跳舞,台下的人也站了起來打拍子。音樂跟節奏都是一首歡愉的歌曲,加上龍太澎湃洶湧的歌聲,令羅伊也開始手舞足蹈起來,現場的氣氛一度高漲,每個人都手牽著手圍著羅伊跳舞,主持人還在後台推出一架手推車,車上載滿一支支注滿「天堂」的針筒。首先是由主持人開始替自己注射,羅伊見狀想立刻阻止,但其他人沒有理會,隨即一擁而上將針筒刺在自己的頸部注射,不消一會滿地都是空空如也的針筒。接著大家又開始跳起舞來,龍太突然像個裝滿水的氣球爆破一樣變成液體,大家也在一片叫囂聲裡溶化,最後只剩下羅伊獨自在台上,腳踩著化成液體的所有人歡欣鼓舞,跳著、跳著,羅伊感覺自己的身體也變得像氣球一樣脹大起來...
「噗!」
已經是第十三天了,羅伊不吃不喝地一直窩在幽暗嘈吵的家裡,燈一直關著,將大廳裡的電視音量開到最大。他獨個兒坐在梳化上,眼目無神地看著電視發愣,劇集裡的主人公用力地擠出爆笑誇張的演技,但羅伊他連眼皮都沒有跳一下,他彷彿像一個密室殺人的兇案現場,死去已久才被人發現的屍體。在梳化旁邊,有一個木製小桌子,桌上擺放著一杯喝乾了的酒杯,一支喝到一半的烈酒,和一支空空如也的針筒。
平躺在木桌的手臂上的針孔還有微微刺痛和麻痺感,羅伊用另一隻手拿起酒杯,脖子仰後一喝而盡。他能清楚感覺到暖流慢慢從喉嚨經過食道滑進胃裡。不久,羅伊全身劇烈顫抖,他沒感到太過驚訝,因為他清楚知道這是針筒的藥物開始發揮作用的徵兆,嗯~這藥是他一手研製的,它是一種比起LSD(俗稱弗得)藥性更加強烈的迷幻藥,服用者會出現幻覺和時空錯亂,甚至能夠製造出虛假的記憶。意識開始漸漸散煥,周圍的聲音變得虛無,眼前的景物開始扭曲,他掃視四周,房間的所有景物就像正在慢慢溶化的雪糕一樣。羅伊閉上眼睛,任由天旋地轉的眩暈感佔據自己的身體,他知道,夢境要開始了...
隔天,警察接到市民電視機音響太大的投訴,羅伊被發現他倒臥在家裡,在破門而入的時候,發現羅伊已經沒有任何反應,只是身體不停地抽搐,嘴角保持著幸福的微笑。警方收集了現場的證物,經過查驗後懷疑是針筒內的毒品所導致羅伊出現這種現象。警方亦指,現場有大量該藥物的大量相關資料文件,細查之後才發現羅伊是個在醫學院的研究生,一直埋頭在研究一種命名為「天堂」的藥,但最後因藥性太強的關係,藥物不被接納還禁止公開對人類使用,亦被判定為極度危險藥物。警方不排除是因為這個原因,羅伊才對自己進行注射。
(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