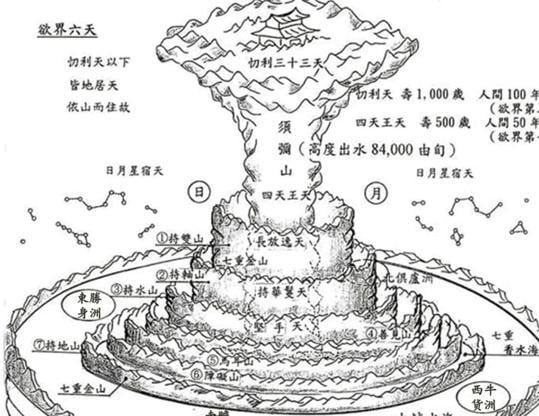婉君把我叫停。塔門郊遊徑偏短,我們離觀景台幾分鐘路程。「幫我看看耳朵,」她請求,「像被蜜蜂咬。」
我藉葉間的光看她耳後。背囊帶壓住她頭髮,我撥開,發現一珠水藍。不是蜂螫,「沒被蟲咬。」我猶疑三秒,然後五秒,四十秒。婉君猛地轉頭,髮絲絲縷縷落下來,遮住運動T肩位,什麼?她用眼神問。
我說:「但你右耳多了隻耳環。」
×
當然,我們沒目睹西貢海,在小徑上返程,到陽光更坦率的地方去照料婉君的耳朵。耳環很平常,是顆耳釘,小如水滴。沒有裝飾,頑固地定在那裡。不正常的僅僅是它無故出現這一點。婉君沒有耳洞,這能解釋疼痛。回九龍的巴士上,我試圖讓婉君輕鬆一點:在台北打耳洞時,對面坐的一家人打舌環。被釘的部位會上麻醉,那家人咿咿呀呀,老少都夢遊。婉君一如既往言簡意賅,應,我該把你舌頭麻痺。
打耳洞後的一天是痛的,但婉君否認。沒痛,沒有痕癢,轉而關心我手上的樹枝擦傷。
下車時我們已商量好不看醫生。理由無非沒人會相信平白出現的耳環;更多的是婉君堅拒就醫。我勸,如果痛如果有異樣就去診所好不好,去私家不去公共、去口碑好的、去年輕醫生開的。她皺眉,如果。我知這是條件句。
×
耳環跟婉君的運動服不協調。再見婉君,約在白石角準備徒步到文化博物館,她穿了長裙涼鞋。
後來我們還是搭車。好罕有,我嘖嘖稱奇,長褲都洗了?運動鞋掉進坑渠?她默默解釋,別過臉:「我無法在知道自己戴了耳環的情況下穿運動裝。」不搭。不符合著裝要求,她在這方面一向嚴格。我挪喻道,如果是隻典雅耳環,豈不是要一世穿晚禮服。婉君沒否認。
我繼續囉嗦:今年Gay ear是左耳,但早已沒人管左右,不礙你性向;美國60年代的學生,一早學會在佔領區被衝擊時把吊墜耳環摘下來;如果不清潔耳洞,傷口會結膿發炎;有耳環特意不對稱;以前我會特地加10元讓店家轉成耳夾......。
×
「我試了脫耳環。」婉君在電話那頭說。不帶起伏的陳述。然後呢?傷口感染了嗎?耳環放在哪?我拋出很多問題。
「不成功。」電話對面是沉靜。臉貼屏幕賣力提問的是我:「什麼叫不成功?脫不下?還是你摸不到?耳環消失?耳環返回原位?」
「脫不下。」 一試圖扭開耳針就痛,且是全身。婉君很勞累了,說話用氣聲。模糊像浸在溫甜酒裡。「不必脫吧?既然是莫名出現的耳洞,不洗也未必有問題......」她聞言嘆氣。只嘆氣,什麼都不講了。
×
不是耳洞的問題,後來婉君跟我說。我意識到自己有耳朵。既然如此,我無法忍受一隻突然出現的耳環固定在那裡。
那時候婉君已經為拔下耳環十分煩惱,或者,疼痛。儘管這樣我仍搞不清她的邏輯。我為耳環辯駁:耳環那麼自然,藍色又美。你大可以穿襯色的衣服,上次的裇衫就很好,質地軟滑。婉君,別為一隻耳環對自己的耳朵發起存在主義挑戰。
婉君莞爾,問,舌上會不會突然多出一個環,手腕穿上一個,腳上又圈幾個,最後,只有無法套環的地方有自由。我開玩笑:所以你很環強。
我們不在這種事上談論自由。
×
我給婉君建議了好幾種方法。包括戴上另外一邊的耳環,但她叛逆。照這個進度我們永遠看不見西貢海了,因為耳環喚起了你的女性自覺,我這樣打趣,你終有一天會提著裙擺跟我去攀山——或者,學梵高吧。這句語氣輕佻。她當然不肯,開始跟隨我出沒在服裝店,百貨公司,看與耳環相配的衣飾。婉君是被逼學會穿衣的,我總是這樣記著。
我們沒讓第三人知道問題。畢竟婉君的耳朵不能成為都市傳說。婉君的聽力沒變好或變壞,但意識到聽力,讓一切都蒙了羊脂般曖昧不清。
罐頭刀都轉不開耳環。婉君右耳第四次流血時,我叫停所有計劃。管他的,跟它相處吧。我默默替右耳包紮,拭掉瀉過耳蝸的血痕。
×
「你要知道,」婉君輕輕念,「你是你。這是我甘心忍受耳環的唯一原因。」縹緲似哦吟。
×
好久以後,直到我們找到房子,定居。我提出領養的問題,婉君在夜裡,床頭燈關了,只餘月光,她幽幽望我,星星潑了一臉。不知我說錯還是說對。
我以為會是自己先作這個要求。她解釋。
「你的性格不適合孩子。」多年觀察讓我很有自信。婉君嘆氣:「不適合,但必須。」
×
婉君幾乎給阿明做了個問卷調查。她堅稱這是為了充分了解阿明是否願意加入這個家庭,至於問卷內容,在我們孩子氣的爭搶打鬧間她從未透露。
阿明第一天上小學,她送阿明到斜坡下,叫阿明自己走到校門口。我躲在某棵樹後,知道這是婉君的風格。
我已預測到,阿明上中學時,她會暗地裡讓我增加阿明的零用錢,偷偷買各式各樣的書放在房裡,等阿明自己發現,去讀。使盡全力又輕手輕腳。
回家那程我們不乘車。多年前的全身疼痛,早完全消彌,從土瓜灣到黃埔,徒步,很簡單。經過紅磡街市她說想看看蔬菜,背過身去。我追上兩步,隱約聽見她唸叨。
這不公平。
×
婉君保留了大部分的書寫。不是因為她愛文字,當然,我知道,阿明也該明白,只是因為那樣更踏實。在一本筆記裡,收藏著我們的遠足路徑,座標,出發日期。
她甚至留下了那些給阿明的問題的紙本。我尋思該不該混在其他東西裡一併燒給她——打開。
阿明不在屋裡。
幾十年前,鳥鳴的下午。所有人都懵懂,這囈語城市,她問阿明的最後一條問題:你是否願意,在我死後除下我的耳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