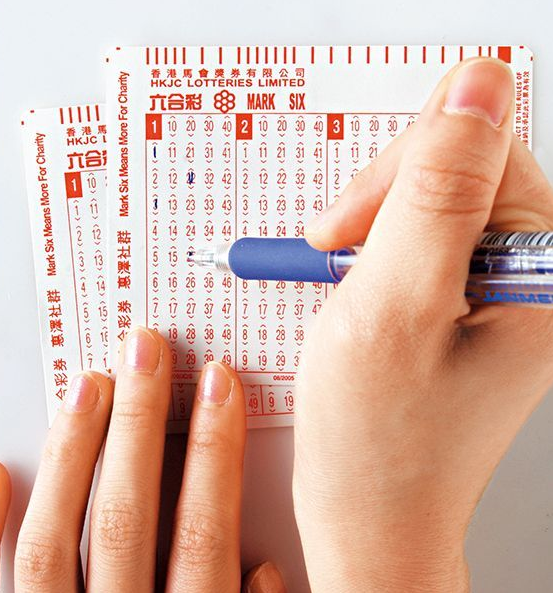如墨的夜,明月微微照亮了一條崎嶇的山路,只見路上一個人影佇立,藉著稀疏的月光可僅僅看出那人的臉孔,是個臉頰乾癟,雙目微陷的中年女人,她身旁還有個不知裝著甚麼的大麻袋。山路是通往一條極為偏僻的破舊村莊,若要從村走向車站,可要走約兩小時。
山路的另一邊,一個男人和老女人蠕步逆村而行,老女人看似是男人的母親,被男人小心翼翼扶持。黑漆的四周埋伏不少危機,一不留神就會失足命喪千岩萬壑,因此兩人都沒說話,專心致志以防踩到碎石。良久,男人開聲,埋怨道:「都叫你不要出來,拖累了我。」聲音甚是沙啞,語氣粗魯,惹人反感。
老女人喘吁道:「這裡是我辛苦攢湊的錢,都給了你,你還說三說四。」男人聽畢,似乎撩起無名火,忽爾爆發道:「沒有我,你還有命嗎?你給那個混帳弟弟出去城市,就不給我去?現在誰養你?他一分錢也沒帶回來!他風流快活,我就在這裡受苦!就是為了那畝皮毛的地,你忍心要我留這裡輩子?」
老女人反唇相譏:「誰把你養大的?誰給錢你去買妻子?你老爹死了,就沒人管得著你這逆子,還拿我出氣......」
「若我是逆子的話,早就把你推下山了!你要知道,我是王家唯一繼後的人,比甚麼都大,你最好就乖乖閉嘴。」男人更大聲,暴躁地回答。
老女人被他的氣焰嚇到,立時默然不語。如此走著,不知過了多久,兩人走到山路的分岔口,隱約看見一個身影叉腰而立,旁邊放著一個大袋,男人歡喜若狂,顧不了扶著老女人,衝了上去。老女人身體突然失去倚靠,跪倒在地。
男人靠近那身影,悄聲道:「是不是陳嬸?我是老王呀。」語氣驟然恭敬得令人雞皮疙瘩,和剛才與老女人對話時截然不同。月光那人的臉孔若隱若現,只看得出是個女人,她點點頭。男人又道:「錢都帶來了,請你檢查一下,你知道我們鄉下人最講究誠實......」男人交出一疊銀紙,笑臉諂迎,猥瑣隨臉上皺紋而現,像是太監,又像一條狗。
陳嬸手指熟練地來回數著紙幣,這些交易每天做不少,早就精通了數銀幣的技巧,十幾張紙幣幾乎只靠觸覺就知道數目,輕鬆簡單。她確定數目後,指著麻袋道:「這裡。」男人興奮地俯身麻袋,把袋口撐大,在月光照射下只看見一片反光黑濛。
陳嬸又道:「這個給你,不乖時很好使,可不要用過量。」把一支極小的膠瓶放到男人手中。男人戰戰競競地收好,又以噁心的語氣奉承道:「怪不得村子都讚陳嬸有保證,果然名不虛傳......」還未說完,陳嬸已轉身離去,男人卻還在揮手,喊道:「小心行好......」
待陳嬸離去,男人的臉方轉向麻袋,「哼」的一聲,吐了口水到草叢,細聲喃喃:「好大的架子。」然後把麻袋的袋口束得只剩下一個小洞,背好,回到老女人旁邊。
老女人早已把身體的泥土拍走,站了起來,男人不屑地道:「你可以行吧?我背著這個,扶不到你。」說罷,逕自向村子方向走去。老女人也只好躡步。
回村時天剛破曉,男人趕快回到家中,急不及待解開麻袋,把裡面的東西放到床上。一個被繩索捆綁的年輕女人。
這個女人仍在昏睡之中,樣子不差,男人心道:「想不到這麼有運,選到個頗有姿色的。」幾十年抑壓的獸性和慾望頓時解放,已理不得為她解綁,當場進行獸行。
「呼......」男人伏在女人身旁,一臉滿足。不久,他回復氣力,到外面裝了一盤水,淋到女人頭上。女人在冰凍中醒來,眼睛半睜半合,男人眼睛直盯,視線沒有離開過女人,直至女人和男人的視線碰撞,女人的眼睛才瞪大起來,瞳孔充滿驚恐,彷徨,不安。女人又看看四周環境,這是一間由磚頭砌好的房屋,殘舊,四方八面的漏孔射入微弱的光線,右邊一個較大的缺口作為窗戶,更多的陽光從此而來,為昏暗的房屋提供少許的照明,折射下,可見到塵埃飛揚,家具只有一個大木櫃,兩張椅子和現在躺著的發臭木床。
女人無法相信眼前的事物,上一刻她仍跟著一個中年女人去面試工作,現在竟在一間破爛不堪的房屋。她再也抵不著心裡的懼怕,想要掙紮,方發現被綁著,無計可施只能大叫:「救命,救命......」
男人「啪」的一聲掌摑到女人的臉上,女人臉頰登時紅腫,痛楚令她停止了呼叫,男人臉目猙獰地道:「我用錢買你回來的,想走?」女人又喊道:「再不放我,我就報警......」仍未說完,男人又打下來,冷笑道:「外面的警察都是我們離村工作的人,你還是放棄好了。」又說:「我現在去耕田,你要是喊一聲,我回來就打你十下。」然後推門離去。片晌,女人平伏下來,想要重整思緒,竟發現下身赤裸而疼痛,眼淚自然地流下。
男人到田裡務農,一個年輕男人走了過來,拍拍男人,笑道:「喂,老王,聽說你買了。」男人一臉得意自豪,不可一世,道:「是呀,還頗漂亮,不過不太乖。」年輕男人道:「我那個當年也是這樣,到時就慣了。」
男人工作完畢,夜晚歸家,聽鄰居說女人有喊,回去二話不說一掌又一掌地打她,直至女人低下頭,噤若寒蟬,才到外面吃老女人煮好的飯。老女人趁男人吃飯時,進裡面餵女人吃飯,女人不吃,老女人為她解綁,安慰說:「當年我也是如此被賣了進來,現在還不是活得好好的?這裡的女人全都是這樣,吃吧。」女人想了想,又是害怕又是不忿,隨後想到逃脫,要保著性命,便張口吃飯。
男人回來,見女人吃飯,以為女人已服從,隨即又做起獸行來。女人沒有感到魚水之歡,只有無盡的痛楚,她在激昂之下默默流淚,尊嚴和自由都在這天被奪去。
兩年後,女人已是男孩的母親,男人卻依舊粗暴,橫蠻,自大。自那天她被揭發想要逃走,被村長行法,便知道這條村子沒有法律,只有宗法,要離開只能靠自己。一天,女人發現男人的櫃裡有一支用裝著膠瓶的藥,讀過書的她很快知道這是迷暈藥,霎時,她想到逃脫方法。
這年冬天很冷,男人很早就回了家。女人見他一回家,便頻送嬌波道:「知你辛苦,我特意為你宰了隻雞,還買了點酒。」男人很高興,又把女人拖到房間親熱起來,女人假意迎合,卻是心中淌血。親密過後,便到外面吃飯,男人先喝了點酒暖身,半醉半醒,全家除了女人,都吃下了放滿迷暈藥的雞,男人尤甚。
「親愛的,吃過飯後我們去......嗯。」男人恍神地揮著酒樽,女人潛意識坐後半個身位,移離桌子。
半晌,全部人倒下。女人毫不留情,立時把男人的厚衣脫下披到身上,並將家中的錢全數拿走。臨行前,不捨地看了一眼熟睡的男孩,便關上門,頭也不回離去。
天氣太冷,村子的人都躲進屋內不願外出,村莊空蕩無人,一片冷清。女人的腳步卻沒有因寒冷而減慢,她走了兩個小時,看見遠方的車站剛有車停留,拼了命直奔過去,她被寒風吹得披頭散髮,狼狽不堪,但她一生中,沒有如此興奮的跑過,她踏上車的一刻,彷佛重拾尊嚴,重拾自由,重拾所有。
她坐在車上,不敢回頭,不敢回望過去逗留過的地獄。
翌日,天空開始飄雪,村莊被染成雪白,剩下安詳和平靜,只是村裡的人紛紛鬧哄,因為這裡多了三具屍體。男孩抵受不著藥力死去,男人沒有衣服而凍死,老女人上吊自殺而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