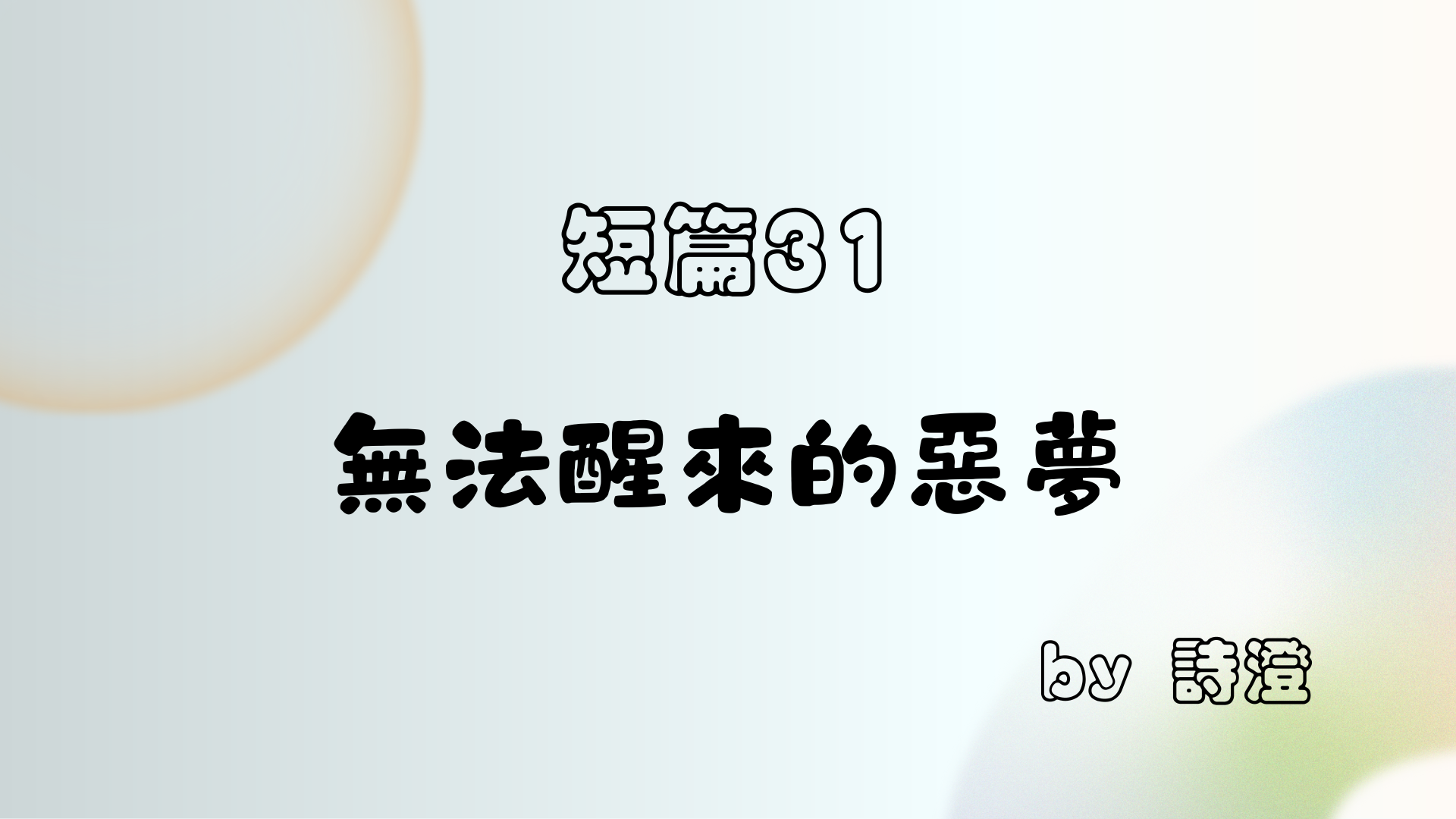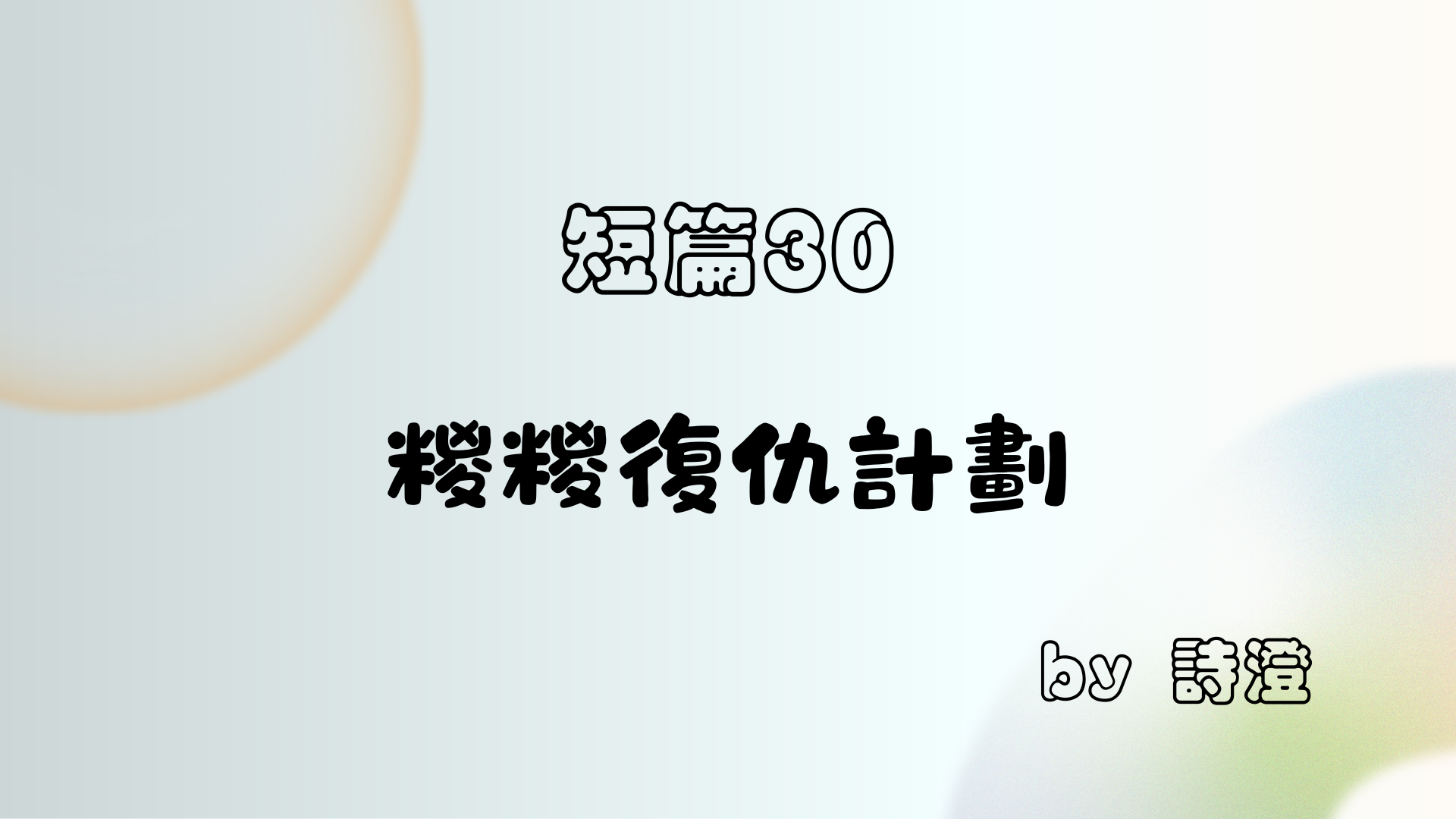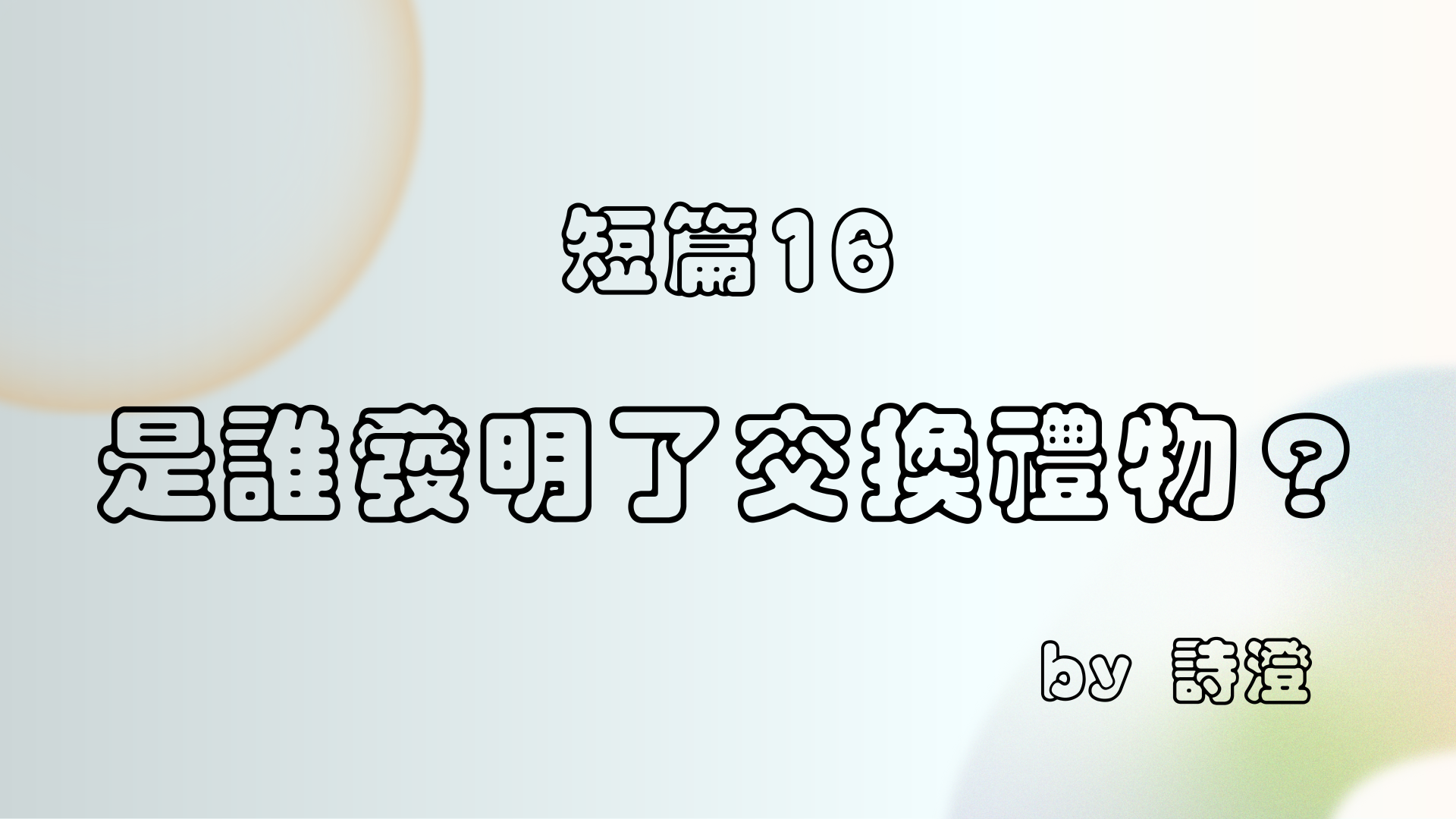當她的知覺復蘇之後,只見一片鶴頂紅,孤清冷靜,卻在漂浮,無重量的自由,她失去溫暖,她失去記憶,她只記得的開端,也許她知道這是一種孽緣,終於是時候結束。
穿起一身鮮紅連身裙的她,再次踏上這條旋轉式樓梯,紫色的地毯誘惑高根鞋發出低吟的神秘呼喚,挑釁在門後等待的人,血液翻騰的幻想,蠢蠢欲動的飢渴滿足。
她敲響掛上207門牌的木門,門後的人打開,她仍然緊張的進入。她是活在這房間的女人,只有在這上鎖的房間,才能獲得生存的基本條件。她每天在這房間出入,對房間的物品、天花與光線、氣氛與氣味都了如指掌。緊張的不自然,是為她打開這上鎖之門的人,永遠是神秘的陌生人,她步步為營,站在牆邊不敢亂動,對方誤以為的害羞更為提起興趣,將她按住,直到無法呼吸。
這次開門的人,卻什麼都沒有,只坐在床邊抬頭望著站著的她。他終於遇見她,她記得的曾經。因為生存的必須要分開對方,而折磨自己。眼淚凝眶,他們都落淚。她忍著悲痛,脫下高跟鞋,上前親吻他,他推開了她。他知道,她在扮演,他不要她的虛假。她哭了,她在他懷內哭了,他把她按在床上,脫下她的連身裙,舌尖喝著她的淚水與汗水,她哭著尖叫,他終於擁有她,可是他擁有她,只有這短短片刻。
他不要她的虛假,他要她一生一世的隨身。他狠狠的在她手腕烙下印記,她痛得昏厥。他把她泡在滿水的浴缸中,任由花瓣染污透明。他終於得到的,是她那被侵蝕的身體,不完整的缺憾,再無法彌補。也許只有在軀殼內的流動才保存純潔,他吸吮血腥,直到時間的結束。
他終於得到了她任何人都得不到捉摸不到的美好。犧牲了軀殼,靈魂活在他的心臟。鶴頂紅是一種毒,他的靈魂最終被她操控,一起飄散於灰塵之中,煙消雲散。再沒有蛇與樹之間的糾纏,與女人之間千絲與萬縷的罪孽。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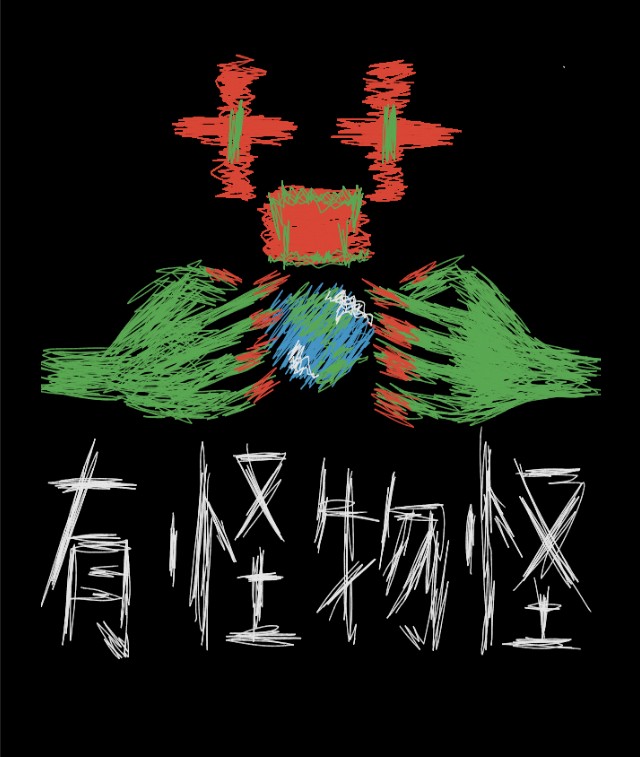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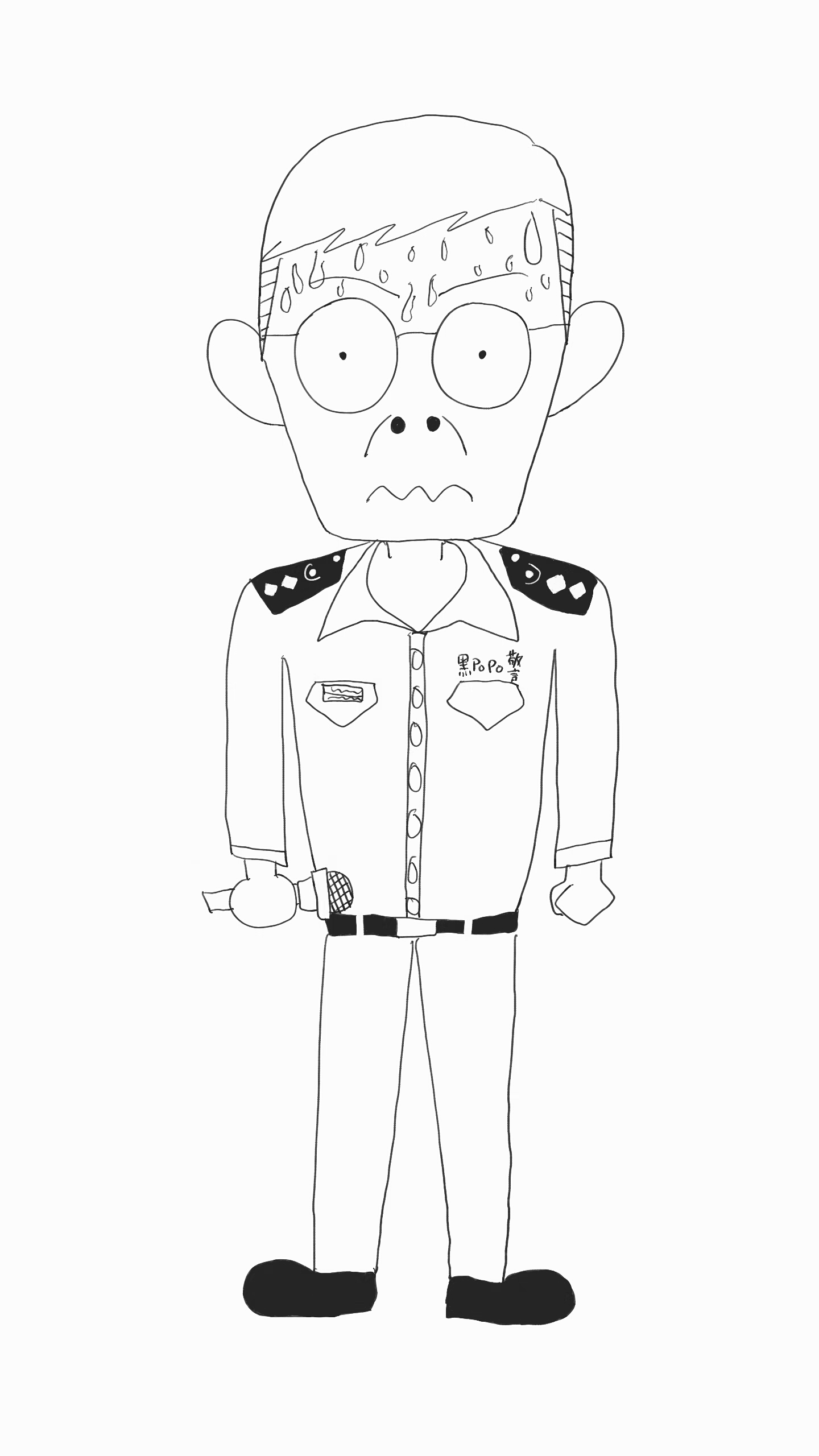
.jpg)
.jpeg)
.jpeg)