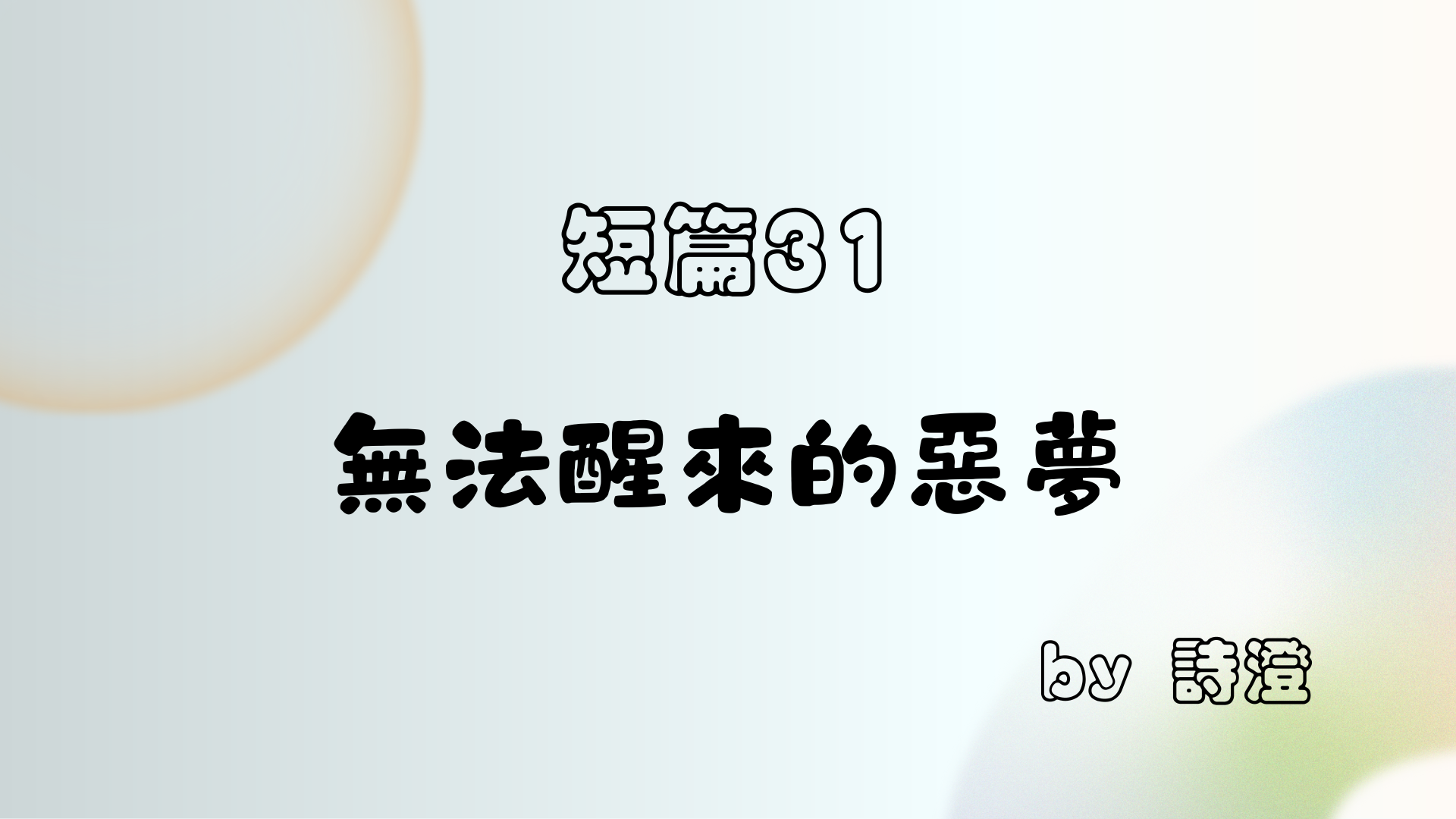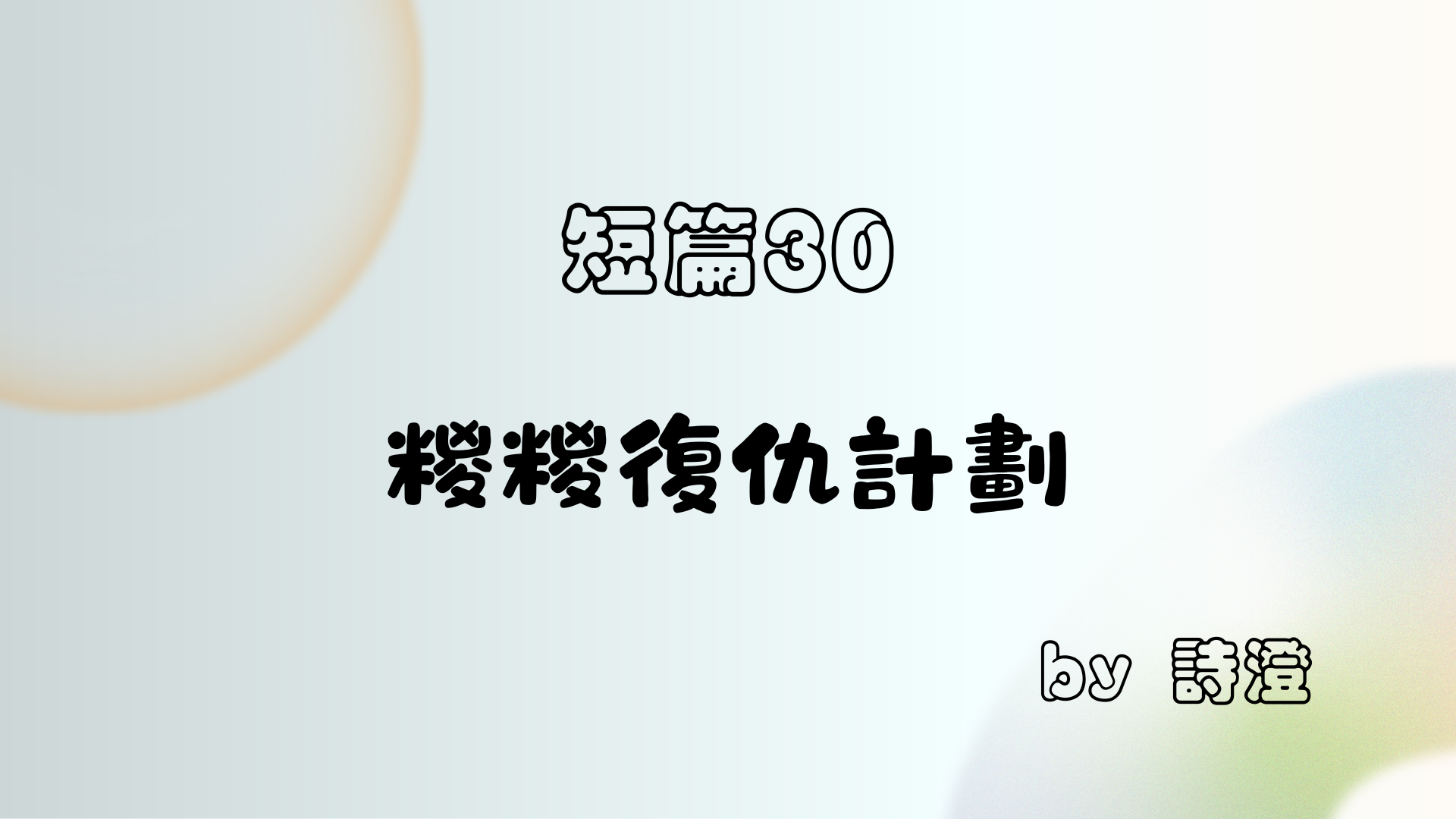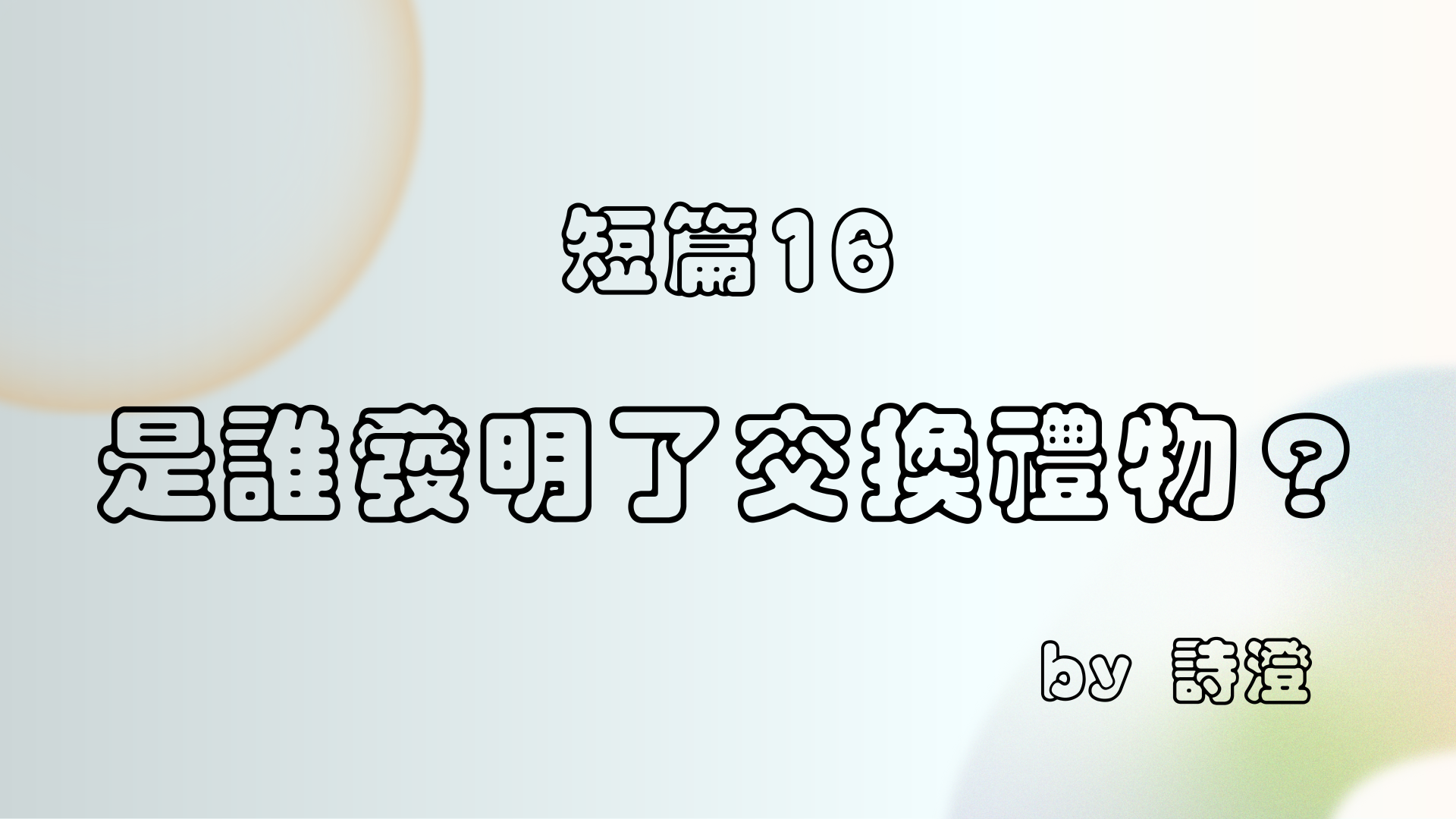「你又摵?」熟悉的女聲穿破耳膜,她像個好事被人撞破的小毛頭,手指對一直在撕扯的頭皮仍舊是戀戀不捨。
從小到大,她總不切實際地渴求著純潔無瑕;面對任何外界之於身體的粘附、污染,甚至侵佔,均不惜一切趕走異物。正因如此,她每天都份外察覺到,那不屬於她本體的異物,那有如畸胎般寄生在頭皮層上的腫瘤。
她把手伸向頭頂,那異物如小丘似地突起著。壓抑著內心的內疚,她的手指開始在異物旁打轉,像趕羊人似的把入侵物趕成一圈,最後連根拔起。好討厭,那些顆粒總附在頭皮上,讓滑溜的表面變得凹凸不平。你只能以手掃過頭頂,確認:是這兒了,然後用留有指甲的手指,像挖土機一樣不留情挖走帶血塊的粒狀。可是,更多的是摸得到卻弄不走,最後徒刮下一層層結霜的屑。
好嘔心。她一邊沿著叢林的脈絡挑走上面的雪屑,一邊口嫌體正直地享受著這頗為頂癮的惡趣味。會有可能接近理想中的雪白無暇嗎?她想。
可能的。尤其蚊叮過後,肌膚會結出惱人的焦。這時候只需要像撕貼紙一樣,一點點把焦從邊緣撕開,直至揭露中間殷紅的一塊,這就好了。身上不至於只剩讓人煩厭的焦黑,而是有殷紅的鮮血證明自己存活著。
「你睇你,成隻手指都係血啦!」女聲再次響起,我嘴角輕揚,輕描淡寫笑道:只不過是我撕開玫瑰時指頭染的色罷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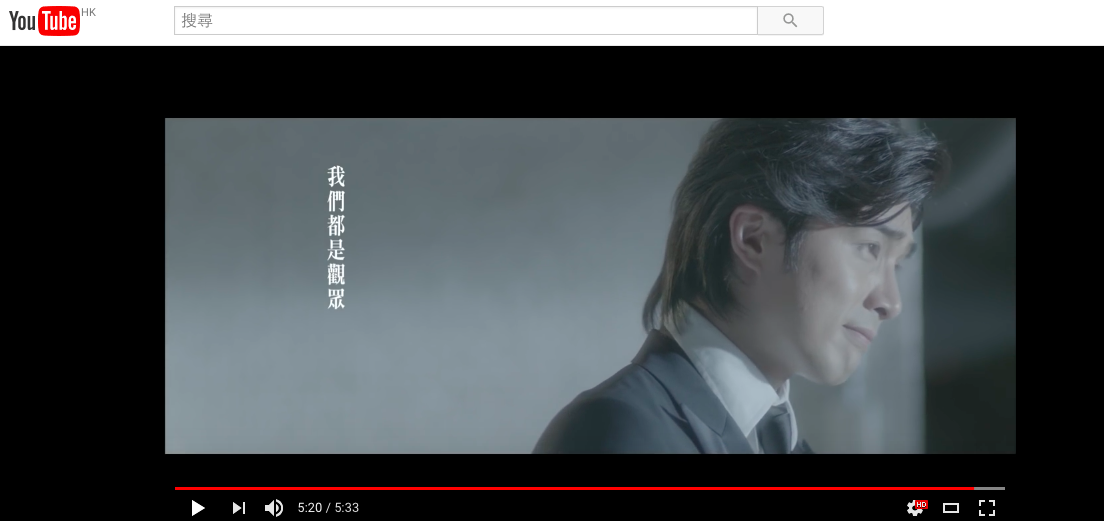
.jpeg)
.jpeg)